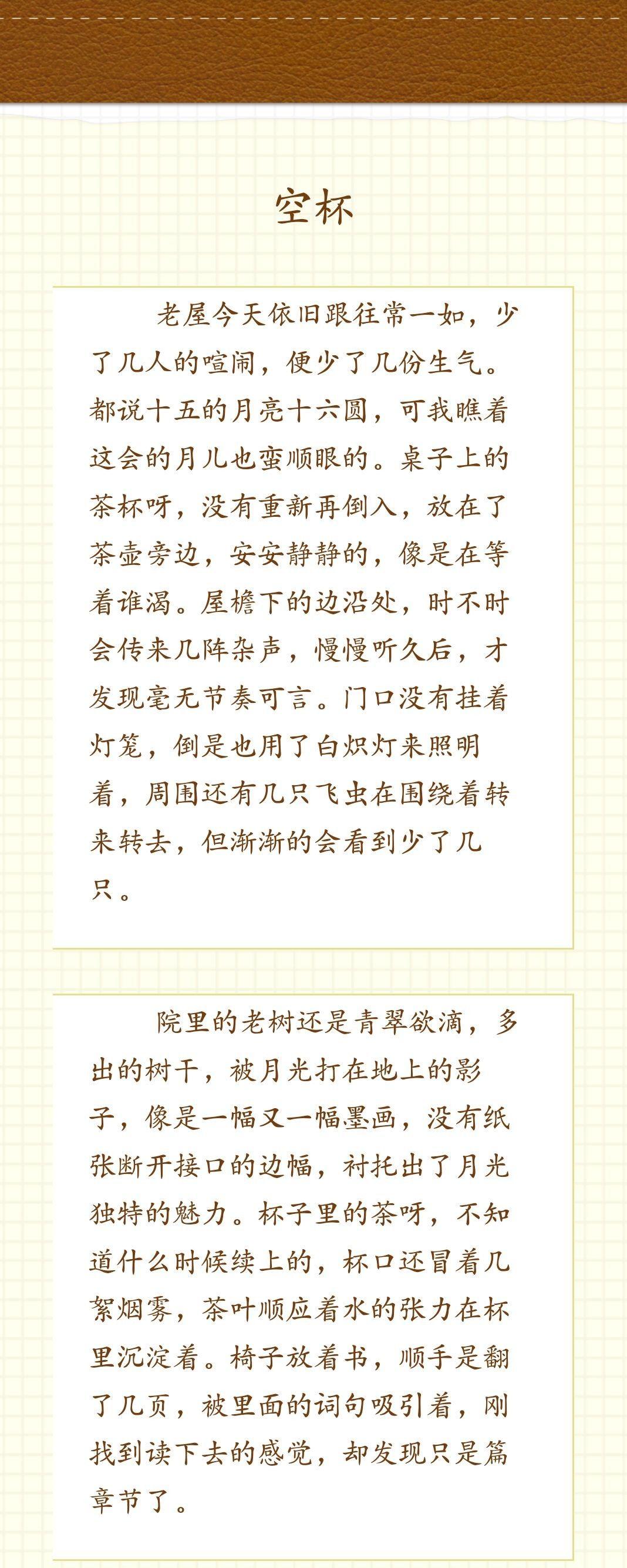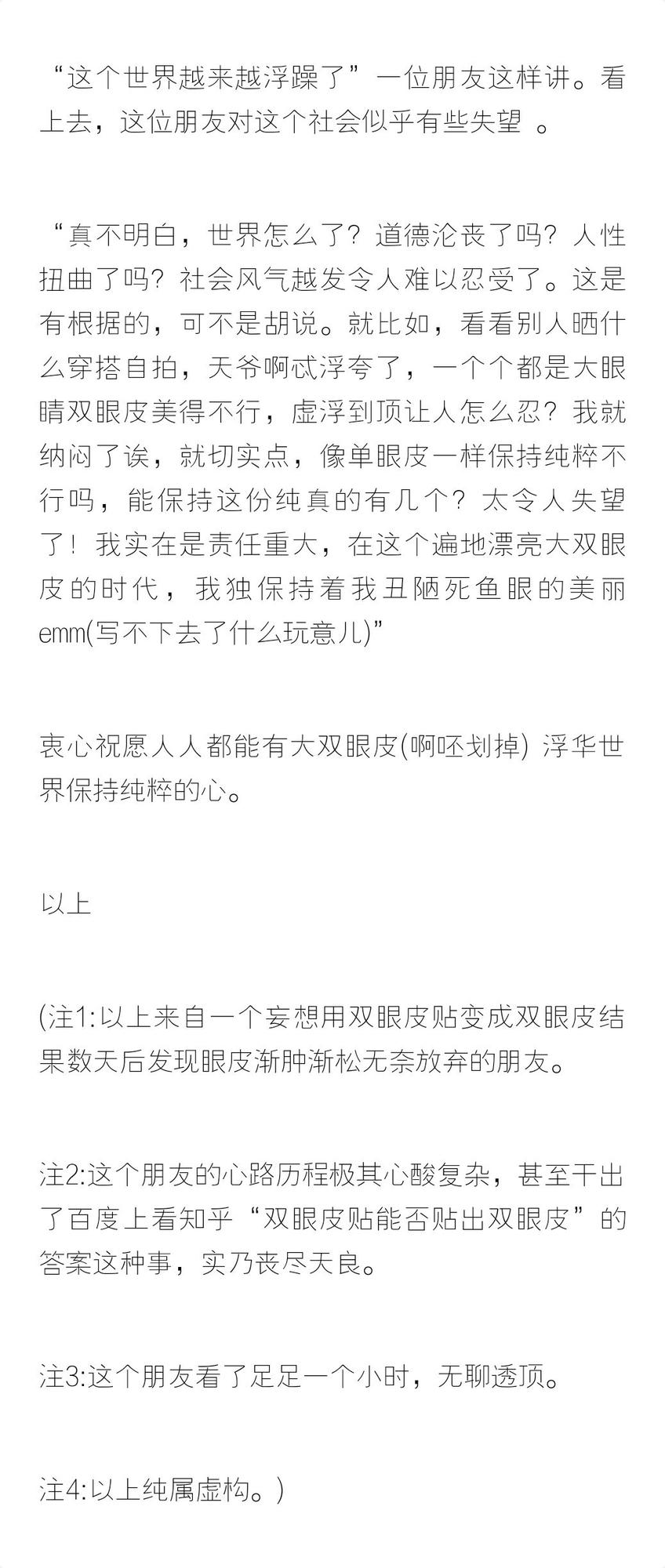即刻App年轻人的同好社区
下载
21天写作挑战
📝你有多久没写东西了?即刻联合非虚构写作孵化平台三明治,邀你每天记录日常,在书写中认识自我
5323人正在讨论,4.7万人浏览
相关圈子

记一件小事
33万名创作者在记录生活
动态
- #21天写作挑战
—— 裸辞后我在自家茶厂当小工
2024年8月,我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状态,我爸妈担心我的身体状况,让我离开深圳回家休息一段时间。爸妈开了一个小小的茶厂,主要是帮助附近的村民加工茶叶并售卖多余的绿茶,每年都忙得不可开交。今年我在家,自然成为了家里的一个现成小工。多年脑力劳动后再做体力活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就像《刀锋》里的拉里去煤矿挖煤一样。这是一件令我向往许久的事情,如今算是如愿以偿。虽说是帮忙,但我能做的事情有限,技术活干不了只能记记账,搬搬茶叶,剩余大把的空闲时间我都坐在机器旁看爸妈忙碌,看来往的村民们聊天。我很喜欢观察人,在观察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想要表达记录的事情也变多了,于是我就坐在小板凳上,记录了这些突然冒出来的文字,我希望他们能为爸妈为这个小小茶厂留下一些记忆,也让更多人知道传统工艺是如何将绿茶加工出来的,以下是今天的记录:
#2025年4月23日茶厂日记
我妈撒茶叶的样子很好看,昨天今天都有客人帮忙撒茶叶,但是看来看去,还是老妈撒得格外好看。多年的训练,我妈撒茶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专业度,端撮箕的姿势,腰弯曲的弧度,手指撒开的恰到好处的缝隙,茶叶在她手里就像是许多绿色的花瓣,手腕稍微一用力抖动,它们就听话地从她手里飞出在空中散开,然后再均匀地落到晾茶叶的台子上。我很多次想拍下她撒茶叶时的样子,但是怎么拍都拍下那种灵活自如的感觉,看来有些美只有在运动的状态里才能更好地被呈现。
一个动作之所以变得美,离不了时间的研磨,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撒茶叶的动作。一个动作重复成千上万次,肌肉便形成了它独特的记忆,如何撒会撒得更匀称,如何撒会更快,如何撒会更省力一点,简单的几十秒里实际上涵盖了太多的学问,只是我妈并不懂得她这轻飘飘地一撒背后有这么多值得人揣摩的细节。此外,这动作里还蕴含着一种不为人发现的自信,当一个老师傅重复做一件事,自然会对这件事熟能生巧,他过硬的技术形成了自己的护城河,他在河岸的那边悠然自得干活,河岸这边的人只能远观,却难以品察出其中的奥妙,更别说亲自上手试了上一试了。我妈就是这样,她不让我插手撒茶叶的事情,说是怕我腰痛,但实际上她对别人撒也不放心,当别人把茶叶都撒成一堆团在一起时,她只能无奈地笑笑,然后口头指点一番,而茶叶继续在她手里开着花,真是好看。
真是不想写加工茶叶的过程,因为可写的真的太多了!但既然写到这儿了,就还是仔细说说吧,这可比撒茶叶的学问还要多。回家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站在锅边向我爸询问了加工茶叶的流程,一共分为杀青——揉茶——二次杀青——炕茶——磨锅五个步骤,是不是很简单嘿嘿,让我上手,那肯定是一个也不会! 因为炒茶最难的不在于记清楚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而是在每一个工序里需要用肉眼判断茶叶的状态,再决定是否结束现在的工序进入到下一个工序。一个字,难! 只有我爸这种喜欢钻研各种技术的人才会去研究一片茶叶的状态吧。
先说杀青吧,茶叶一但入锅,我爸就要寸步不离,在杀青的时候他要守在锅边,时而用手中的小瓢到转动的锅里接一点茶叶出来看看,至于在看啥我也不知道,大概就是根据茶叶的软硬程度和气味来判断杀青到位了没有。我记了一下时间,正常来说一锅茶叶大概杀青五分钟就可以出锅冷却了,但我妈说这个时间不能记死的,要根据每家茶叶的情况来调整杀青的时间,而到底什么样子是杀青杀好了,决定权都掌握在我爸手里了,当他把开关一推,我妈就知道杀青完成,就得提溜着家伙什去取茶叶,取出来的茶叶要撒到台子上放凉,准备进入下一道程序。
第二步是揉,这是我最喜欢的步骤了!打小时候我就见过我姑妈做茶,那个时候在茶厂玩儿,看见揉茶机就走不动道儿了,看它揉来揉去的样子真是爽歪歪,当时还不知道它叫揉茶机,所以我称之为waiwai(“摇”的方言)机,因为它总是自己摇来摇去转个不停哈哈。揉茶的时间是比较久的,如果不赶时间,最好揉上一个半小时,如果来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在排队等候的话,时间会稍微减短一点。揉茶不是把茶叶丢进机器揉就完事儿了,揉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把茶也揉细,揉成细条,这大概需要半小时,当茶叶成为细条后就要稍微加压,将细条压紧压实。等茶叶变成紧实的细条后就可以拿出来,准备进锅进行二次杀青了。
二次杀青、炕茶、磨锅三个步骤都是在同样的锅里进行的,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时间的长短以及火候的大小。这也是我觉得自己学不会炒茶的原因,一个做豆腐都能做糊的人,你能指望她去控制茶叶的火候,那估计要连茶带锅都烧个精光!我爸给我仔细说了锅的火候大小,但我忘了…以后补充再说哈哈哈。有件事我觉得很很妙,就是控制火候大小,我问我爸这个火到底要怎么样控制,它不是纯机器监测调节温度,而是像做饭一样通过添加木柴来增大火力,但如果火大了锅里温度高了咋办嘞,我爸说那就用水,我这才留意到在柴旁边还放着几瓶水,瓶子上钻了许多小孔,如果火大了就往灶里撒水,这样火就会变小,温度也就降下来了,整个过程都要靠人的眼睛和手去观察、感知和完成。不得不说,我对我爸的佩服又上了一层楼。在整个炒茶期间,我见过的唯一高科技就是一个温度计,起初我不知道那是温度计,我老是看见我爸拿着一个手枪一样的玩意儿在锅前晃悠,手枪会射出一道红光到锅里,我妈说那是温度计,好吧,是我见识短浅了,还以为老爸全靠手去感觉锅里的温度嘞。
当茶叶进入到磨锅的步骤时,大家紧绷的神经才稍微缓和下来,因为磨锅是炒茶的最后一步,磨完锅等茶叶冷却就算加工完成了,大家乐呵呵在看着自己的新茶,爸妈也会取来热水和杯子,一起尝尝今年的新茶如何,喝完茶,打包抽真空,一锅茶叶的加工这才宣告结束,而呼噜呼噜转的锅和揉茶机还在迎接新的茶叶,开启新一轮的运转。 21 121
21 121 - #21天写作挑战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最近空闲时间多,去探店。饭毕,赶地铁。因为,时间晚了,这是地铁末班车。
步履匆匆,人来人往,前拥后挤的地铁里,形形色色的人,都在为生活而奔波。
有随便带着公文包的OL职场女性,有正装的小哥哥和小姐姐,有穿着职业装的地铁工作人员...但是,令人瞩目的是她☞一位背着小孩的麻麻。
手扶梯☞她左手扶着的是安全,右手提着的是生活。她,让人心生佩服。因为,她看起来年纪不大,就是娃娃脸的那种,特别朝气蓬勃,真好看。小盆友也很萌,懵懂的大眼睛里面充满大大的疑惑既视感~或许,此刻的他才是最安全最可爱最天真无邪的。
☞见的人多了,越来越喜欢小孩。不为别的,他们的世界真的好单纯。前一秒闹别扭,下一秒就和好。简单粗暴而又特别美好。就是那种小美好。之所以会说是小美好,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可爱!就像那天,在路上,两个小盆友在说话。一个抱怨说有人欺负她,一个说那你骂回去!然后她说我骂了那个欺负我的为王八蛋,他就生气了!然后小男孩就很小声(其实我可以听到,哈哈哈哈哈哈,自认为他说得很小声的小男孩有点声情并茂!!)☞那你叫改一下,叫他荷包蛋。女孩👧☞对耶,这样他就不知道我在骂他了!然后两人对视一笑,特别欢快去了幼儿园!!突然就觉得小孩子的世界好简单,真好。
所以,请问这种懂事的小盆友是在哪里领取的?麻烦联系一下我?好吗?在线等,挺急的。🤔
 18 140
18 140 - #21天写作挑战 吾之济南印象
济南,黄河从北过,泰山在南边
齐烟九点,明泉遍布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此皆地势自然古人留墨
鄙人久居于此近三十载 谓之家乡
前数十年得脏乱差之名,近年天翻地覆,城建进步神速,又得全国卫生文明城市之名,加之历史人文深远流长,实乃宜居幸福之城
此城居民安稳祥和,生活慢条斯理,节奏平静,闲来马扎撸串畅饮扎啤,喝茶聊天次次牛逼,颇有与世无争,不求上进之意
景色古今皆有,处处值得一去,明湖畔有雨荷,趵突三眼齐举,更有千佛巍巍小山,俯瞰泉城处处楼宇
济南城气候将算可以,夏天晒吐露皮,冬天冻不死你,唯有空调暖气,才活下去之勇气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来了她定然不会亏待与你,也断不曾有多少惊喜
一座城,一段记忆,一场旅途,一个印记
在下,等你……
@三明治
 10 40
10 40 - #21天写作挑战 //给对方建立良好信任的准则:先暴露自己的一些缺点,再逐渐建立信任。
//增加信任的途径:做事超预期、立场选择
//对方给你的信任越多,表示在对方放眼里,你展示的东西越真实(越像人民币)。
//信任越多赚钱越多
//IP的销售部分,本质上自己给对方的的信任,而增加信任需要拿些论据论点来论证我自己很行,让对方放心相信自己。
//主播是如何制造信任?通过群体效应(大家都打111)、能力背书(自己给人的感觉有自信,说话给人的感觉抑扬顿挫)、说明自己是个大主播、眼神坚定可以传递给对方的信息是这个人很靠谱,可以相信。表达能力:语言有条理(首先然后其次最后),有例子。让对方有更多的确定性。
//脑子越用强,达尔文的用进废退
//交易发生的基础信任。
//将自己的内化系统改为这两步,第一步输出倒逼输入第二步将学习到的东西实践出来
//自己足够强的话,可以赢的更多的信任。
//赚钱的核心缓解环节“卖”。IP是卖的工具,卖的成本够低,且环节足够的少,也近一步加剧了财富的积累(马太效应)
//做IP主动拥抱不确定性。让自己增加信息的新生活方式。互联网是变化最大的地方,为了应对不确定,自己就要不断的学东西,让自己有立足之地。1 00 - #21天写作挑战
村子里的你我他草稿版
我的邻居
村子相比城市里的小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邻里关系。
远亲不如近邻,村子这种构造,让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和睦。低头不见抬头见,平时白天出门打个招呼,晚上坐路边聊一聊,邻里关系的和睦就在村子里这种没有多大现代化的环境中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家同样如此,南邻居是我们家同脉亲戚,关系好那是必须的。西邻居挺友善,家里卖菜,还经常送我们点。偏偏,北邻居就没有那么和睦了。
北邻居自从我们搬到老宅子之后就是邻居了,规划完之后依然是。主要成员是一位妇女和她的两个双胞胎儿子。男主人基本上不回家,听说一直在外面工作。
北邻居给我们家最大的印象就是哭声,从头到晚的哭声。没错,就是体罚,妈妈打儿子。别看孩子妈妈看着挺瘦弱,但是打起来是真的狠,虽然见不到,但是孩子哭声是真的大真的惨。
晚上村里人瞎聊的时候,他们都说是因为孩子不老实,老是惹祸。可我还是有点不理解,再不老实也是自己亲生的啊,下手也太狠了。村子里其他人可能只是知道打孩子,我的卧室可是紧挨着他们家院子的,无论春夏秋冬,无论白天晚上,那个哭声啊,都让人担心打死了,想要报警。
其实他们家很像单亲家庭,只有母亲一个人带着俩孩子,父亲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这对母亲和孩子来说肯定都不是好的现象。虽然他们家很有钱,特别有钱,孩子他爹每个月发的生活费都快比得上村子里普通家庭一个月的收入了。但是众所周知,充沛的物质生活不等于精神世界的发展。可能棍棒底下出孝子,但是,到了邻居这种等级的棍棒教育,我是真的担心她的两个孩子的未来。每次她打孩子,我和我姐都感慨,这女的疯了。
现在邻居的孩子大了,成绩很差,都在技术学院。不过孩子他妈也不打了,可能也打不疼打不过了。可是因为以前就产生的印象,他们家和邻居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不好。可能就会这样一直不好下去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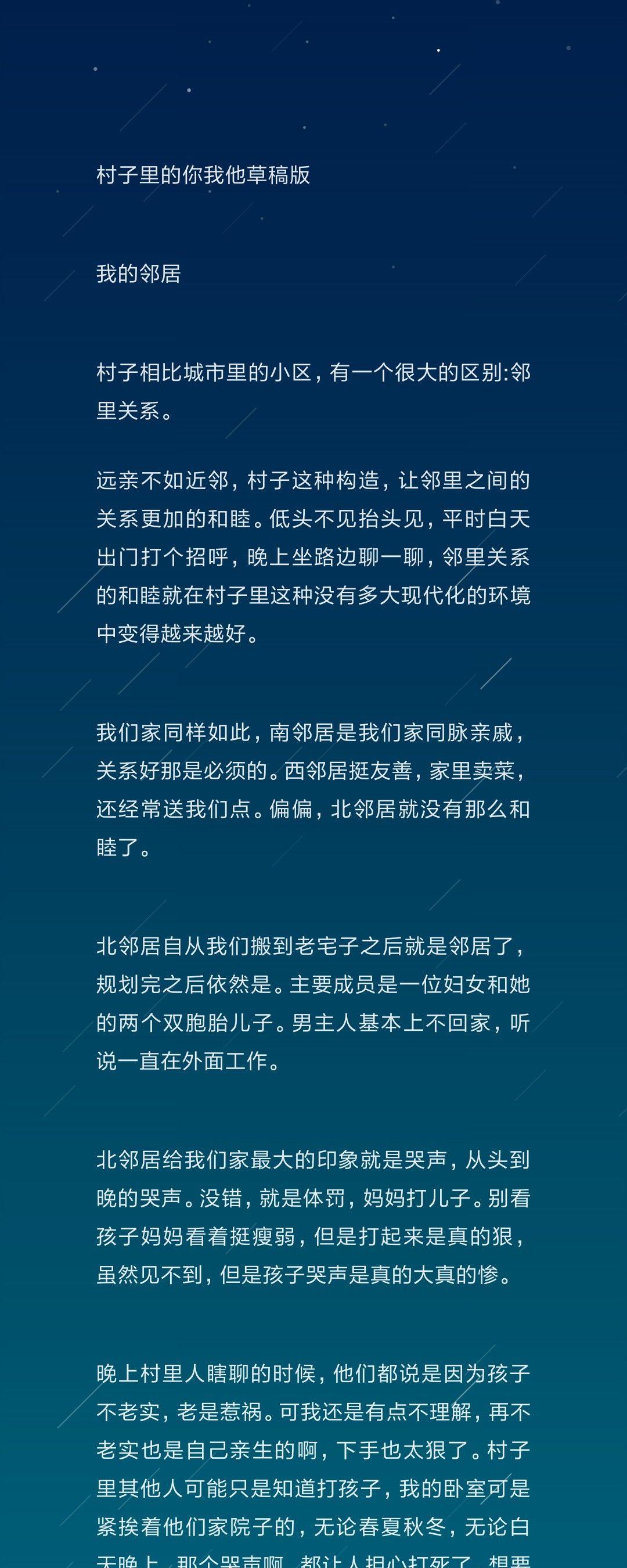 3 00
3 00 - 在遵义有一个县叫南白,后来改名为遵义县,又改名为遵义市播州区。
这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城市,对会说方言的人来说,它是亲切的故乡,是不带伞可以随便进入一家店躲雨的地方。但对不会方言的外地人口来说,这里着实是并不太友好。
13岁因为这里有录取率全省第一的高中,我来到这里求学。却没有想到老师讲课用的都是方言,花了半年时间学语言,文化课却跟不上了。在父母眼中,这都是借口,学不好就是我自己的责任。
班主任操着方言跟我说,我太不懂事了,想要获得平等的对待就让我的父母来送礼。我选择了拒绝。第二天,我的座位就被安排到了垃圾桶旁边。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开始恐慌、失眠,甚至无法正常说话。到了高三那年,我连学校都没办法去,只能躲在家里,躲在被子里。
最后我踩线考上了一所蛮野鸡的大学,但这跟学校没有太大关系,是我运气好。
毕业那天,要拍毕业照,跟我关系不错的同学说“来留个影吧”。我抱抱她,说“你去吧,我记得你就好了”。
后来同学们拉了微信群,把我拉了进去,然后他们好像忘记了曾经发生的一切,要大家集资一起去拜见当时的班主任,我没说一句话,退了群。
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可能我压根没有融入过这里吧。
#21天写作挑战4 60 - 现回头看新冠之前的碎碎念,才真是“今夕是何年”啊。
北京开始冷了,通常有这样体感的时候,是在厦门的冬天。刚刚身体有个打寒颤的瞬间,一度以为下一刻自己是要去超市买个热红薯再去公寓门口打包一份加蛋加肉加中辣的老张拌面,好像是肌肉记忆那般的熟悉。明明是秋天萧瑟的季节,可身体凉意连带着生活习惯的记忆,有种恍若不知何年何地的错愣。以前常常会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可只要密集地在一个城市生活过,暴雨天如何讨厌飞蚁,天气转凉时喜欢去哪里散步,下课后如何不耐烦地等着公交等等这些都带着独有的情绪记忆储存在身体里,日子就一点也不短了。冷不丁地回望下那些承载着自我的生活轨迹,漫漫人生,漫漫人生,原来说的是即便做好准备,好好告别,也仍有戛然而止的“今夕是何年”的年轮感。5 21 - #21天写作挑战
旧事重提。
总有那么几天会失手把床边的书打翻了,啪的一声砸在地上,不知楼下的邻居哥哥有没有被吵醒 ,当送他的闹铃了。还有五分之一就要看完了,开心,大部分都是上下班路途 地铁上读的,沉浸其中就像有了一道保护自己的屏障,对面孩子的啼哭声 情侣之间的争吵,通通听不到。而在家更喜欢看电影和喜欢的人聊天,如果他不在 那我可以去学煮菜。之所以也放床上,是睡前也会翻几页,这本类似游记的书,帮助做美梦。
起床了,买东西不懂节制 很不好,刚去清点储物柜,五条牙膏 四瓶漱口水 三盒面膜 这只是冰山一角。一转脸还有没看完的各种杂志,上面有酒渍 跟我的牛仔裤一样。嗯 看杂志也不喜欢在家 喜欢坐吧台,在taproom很放松 把手机丢一旁,坐那看上去就个奇怪的人,除了老板 只有胆大的人会来搭讪,我怕麻烦 懒得应付。有一天喝的不是很大时候 刚放下华夏地理,吧台旁边的客人随口问我在看什么 为什么爱喝酒 我说 两个问题 应该先满足哪一个好奇 但不管怎样 酒鬼的标签我不承认哦。
他可能也喝迷糊了,又问我知不知道村上春树 我说嗯 “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他讲这个作家处女作《且听风吟》时就是经营酒吧下班时候写的。我说 嗯 所以呢。
他说加个vx吧,我摇摇手 你喝醉了。
刚刚刷动态看到 他是个物理老师。9 10 - #21天写作挑战
都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但我第一次认真听法语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感觉,心里念叨着,比起法语,我更喜欢英语。
开始强烈产生想学法语的愿望,是在摩洛哥玩的时候。因为要进撒哈拉,报了一个三日的沙漠团。同行的一对情侣,一个是在牛津读博的英国小伙,一个是美丽可爱的法国姑娘。像极了《爱在》三部曲里的男女主,他们总是吸引着我的目光。在进沙漠的巴士上,男生全程很安静的拿着Kindle看书,女生则是兴致盎然的看着窗外。路途上,我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他们聊着天。跟团的导游会五六种语言,并且还告诉我说,这不算什么,这里还有很多人会8-10种语言。但实际情况是,我遇上的多数当地人英语水平并不好,甚至有的还不太会说英语。除了阿拉伯语,法语是这里第二大通用语言。看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时,还以为西语才是这的通用语。因此在巴士经停的地方,可爱的法国姑娘总是可以顺利的和当地人沟通、买东西或点餐。对了点餐,有一个餐厅的菜单只有法语而没有英语。刚坐下时我还试图拿着翻译软件拍菜单,但翻译的结果实在是令人头痛,于是放弃。转向坐在旁边的法国姑娘求助,点了她推荐的菜。
意识到还有其他国家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后,回到伦敦马上就报了一个初级的法语班,老师是法国人。说是Beginner level,但是从第一堂课开始就是全程法语教学,而我全程懵圈。才知道原来很多英国人或多或少都有掌握一点法语单词,上了两节课后才慢慢适应。课程不长,总共就十节。课是上完了,但学的东西没多久也就全还给了老师。之后的一次法国行,想着一定要用上两句法语才算对得起这十节课。到了法国,在我对一位当地人说出了Bonjour以后,对方以为我会说法语,一脸惊喜地回了我一长串句子。本还期望着按课上学的内容对话两句,一下又把我憋回了英语模式。法语好难。
下个月要去瑞士玩,会到瑞士的法语区,于是这几天又产生了学法语的动力。下了法语的App,翻出以前Youtube上收藏了但一直没看完的法语教学视频,不知道这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能学到什么程度,但如果除了Bonjour之外还能再多说一句法语,也算是对得起我对这门语言的执念了。(希望不是一个打脸Flag)61 221 - #21天写作挑战
当吃尽最后一颗荔枝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整个夏天的漫长,这种漫长不仅是时间意义上,它同时包含有灼热的空气,无比漫长的白昼,以及在城市的硬化路面间四处穿梭的无由焦躁。
自从毕业之后,已经很少回家了。而再度谈到回家的时候总会怀念一些不着调的东西,像是极美味廉价的西瓜,浑浊的云,混杂着榄仁和别的东西的香气,十几年未曾涨价的早餐,阳光与灰尘混合升腾的气息,田地中每一种作物的生长周期,这些记忆二三掺杂起来,像是在向我呼喊有关家乡的一切事实
这些年来,归家的列车每每中午从广州出发,到达河南时已是傍晚时分。再向北时干燥的空气中闪着繁星点点,偶然见到城市边缘的金色剪影,那是路灯,是光,是未冷的阳光,是连绵的烟囱,是一闪一闪的烟花,是道路最终家的方向7 10 - #21天写作挑战
今日红
----三明治披萨女孩
天气 晴 宜 金桔柠檬
(昨天的对话)
one:“下暴雨了!”
“是,我的浅色牛仔裤变成渐变色了!”
“………”
“你,去洗漱吧”
(今天的communications)
two :“中午吃什么”
“想吃水果”
“要帮你带西瓜吗🍉”
“我要西瓜🍉桃子🍑葡萄🍇”
“我回宿舍了”
“……”
three:(隔壁寝室姑娘跑来聊天)
after她们聊了很久爱情
巨同学:“你觉得你20岁以前能有初恋吗?”
迟同学:(目光怜悯看着我)
杨同学:“我以为这个对话我不用参与的”
巨同学:(孺子不可教也脸)
迟同学:“我以前在抚顺的时候那个对象啊…”
杨同学:“我们点个抚顺麻辣拌吧(饿了)”
巨、迟同学:“……”
four:学校的猫猫霸王 6 20
6 20 - #21天写作挑战
我有时候对这个世界充满怀疑。
在我的膝盖准确撞到床沿的时候,在我的内衣从楼上掉下去的时候,在别人大声跟我说话的时候,在我吃冰激凌不小心用了牙的时候。
今天很不讲道理,在我奶奶跟我吵架我又去哄她的时候。
我忘了我们为什么吵架,大概是她迷信、还要逼着我说服我爹跟她一起迷信的时候发生了矛盾。吵完之后她躺在椅子上,做出一副永远不和我和好的样子。我也非常硬气,坐在她对面,把李子咬得很响,她尴尬的吞口水,又碍于面子继续马着脸躺得端正。我心里已经很爽,但还是没忍住:“你还咬得动吗?那么馋。”
她报复似的两手撑直身体,从果盘里抓了个最大的,立马塞进嘴里。我立马就消气了。乐的。
我哄她:“别生气啦,生什么气,你看你也骂我了。”
她阴阳怪气:“我哪儿会生气,咋敢生气。”
我沉默了两分钟,然后她偷看我。
我说:“你看,我都哄你了。”
她说:“这就完了?”
“那我再给你一个李子。”
“我自己不会拿?”
“那你要我怎么哄?”
“用不着!”
……
女人一辈子都是女人。11 80 - #21天写作挑战
(随便写写,观点不明确,逻辑不清晰,可能会引起不适,接受私聊批评 ヾ(´A`)ノ゚)
和朋友聊起来鬼魂和死亡的问题,虽然被穷鬼,色鬼的朋友给戳上了笑点,但还是被这个问题带入了深思
在小时候一直都被灌输,死亡是逝者与生者所在世界的告别,是去往了另外一个或好或坏的世界的开始,比如天堂,地狱,地府,极乐世界等
但是现在仔细想想,不能说这些说法是对是错(毕竟可以不信,但不能不敬畏)。但是这些说法基本都是建立在人们对死亡的敬畏和劝导人们向善的基础上,所以个人还是赞同这些死亡的解释。
但在抛开感性因素的影响,死亡到底是什么还是挺耐人寻味的,虽然有借鉴他人思想的嫌疑,但是从人的属性来说,在逝者葬礼的那一刻,便是人自然属性的消亡,便是从作为一个自然人,一个生物,从自然界的离开。而当逝者从生者的记忆中消散之时,应该就是作为人的社会属性消失的时刻。当这两层属性的消散完成,我想就是“死亡”吧。
常言道,人活一口气。有人说这一口气是人的灵魂所在,我从内心上是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因为确实有难以忘怀的亲人,我希望他们可以一直存在。但是这“一口气”是否是灵魂,现在也没办法验证。不过,现在让逝去的人活在记忆中,在我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而有的时候,让“另一个世界”来聊以慰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吧。 3 00
3 00 - #21天写作挑战
每天从家到公交站,从公交站到公司都有一大段的路程需要步行,所以关于我的一件小事的素材来源很多都会取自这些地方。
和许许多多的上班族一样,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工作,而不高不低的工资成为了压死激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只剩一息苟延残喘的抵抗,可笑又可怕的明天每日都会如期而至,没有惊喜,没有反转。没有了再次面对找工作的勇气,亦少了潇洒辞职的魄力,更多的时候是安于现状的耗着,想改变却又无所作为,心气高却又没有与世界抗衡的资本,充斥着矛盾与反复无常的脾气。
好像写的太丧了,下半年我希望能慢慢地放开自己,逐渐敞开心扉,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2 10 - #21天写作挑战
今天又是美美的一天。
我和男朋友太低估贵阳人对丝娃娃的热情了。工作日大中午12点半开始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才轮到我们,吃完了两点,过三点了还有好多人在排队。
如果有外地来的朋友,一定要推荐一首贵阳特产丝娃娃。除了有点素,简直是完美。如果没有本地人的带领的话,不知道哪家比较好吃,那可以来这家“丝恋”丝娃娃,他们家汤是比较特别的(酸汤),而且也比较好吃,小吃的品种也特别多,在他们家里可以吃到很多贵州的特色小吃。就是有一个确定,有点贵😂,差不多人均50。







 11 20
11 20 - #21天写作挑战 *四*
做了一天的功能设计说明,逐渐梳理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还存在着很多不足,没有形成一套标准化的产品思路。
但同时,我也在思考,我们不想被工作中的标准化限制住自己的思维,不想被千篇一律的生活固化自己的活法,那究竟应该怎么保持既能标准化的工作,又能自由自在的生活呢?
产品经理们总是在讲业务逻辑,痛点,痒点这些听久了越发觉得恶心的词汇,而这些词汇,由一些好像是可以被复制的成功者们把他们的思路标准化后,逐层普及下来,给我们这些低级产品人使用,并逐渐成了一门学科,逐渐普世。
使得被这些理论侵蚀的产品听不懂,也不想懂人话。正在被侵蚀的产品,逐渐不会讲人话。然后在他们的某个工作节点上,把这些成品或半成品的思路和过往的经验混合,搅拌,封装成了自己脑子里的核心库,再慢慢继承给他的下层产品们,最后大家其乐融融的一起成为二半吊子的产品人。
嗯,我的生活已经够糟了,不想再挂上二半吊子的标签。
所以,戳聋耳朵,换个活法。2 00 - #21天写作挑战
[ 多情的人和多情的狗 ]
故事还是发生在我租住的小区,有一群无人看管的流浪狗,其中有一只跟我挺有缘份,我叫它“小白”,因为它的毛色是白的。
小白跟小区里的其他流浪狗有所不同,小白跟它们在一起玩却不在一起住,其他的狗窝在一堆,它独自守着隔壁大楼的一处小角落。那是大楼门口的一个地方,有瓦遮头,无论风雨,它都回到那里,就像在等它的主人。
观察了它很久,有一次回家,它跟着我舔了舔我的鞋,然后我们眨巴着眼睛互相对视,自此以后很多次回家我们都会重复这个动作。
每次吃完饭我都会故意留点饭菜端到楼下给它吃,吃完它就回到那个为它遮风挡雨的地方。直到有一天晚上下大雨,我听到门外的咦呜声,我猜是它。推开门一看,它果然窝在门外。是的,小白不知道为什么不像其他的狗一样大声的叫唤,只能小声的咦呜着。我觉得很可怜,似乎是有什么困难才找上门,又有点手足无措,不管它也不是,领回家也不是,幸好门口的那个角落也不会让它淋到雨。
第二天早上,我担心着推开门,小白还在门外,看了看我就开始蹭邻居的门。后来我发现,原来是邻居养了一条狗,每次去遛狗,小白就会跟上去,甚至也跟回了家。小白是上门追寻伴侣来了,嗯,我这愚蠢的人类。5 00 - #21天写作挑战
雨
今天成都下了好大一场雨,断断续续的持续了一整天。
我的工作没有假期,但下雨便是我的假期,因为下雨会使得工地变得泥泞,挖土会塌方,车辆会陷住无法自拔,工人不想淋雨工作。
今天我使命便是在活动板房里等待吃饭。
上午等待午饭,下午等待晚饭,傍晚等待夜宵。
真是难得的休息,什么都不想做,就连和心爱的人通话都觉得麻烦。
时间一晃而过,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发现自己荒废了一天,什么也没得到,什么也没失去,仿佛就像有人拉了我的进度条,直接从早上拉到了晚上。
雨还在下,而我的进度条却不多了。3 00 - #21天写作挑战
今天那个“疯子”又来我家门前的水龙头装水喝了。我们镇管精神不正常的流浪汉叫“疯子”。
在我小时候,我一直以为“疯子”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流浪汉的特指。镇上大人最常吓唬闹腾小孩的两个把式就是“不听话猫子就会把你抓去走”和“不听话‘疯子’就会把你抓去走”。“疯子是和怪物同类的”,小孩们理所当然地想着。我只是这个镇上的一个普通小孩,所以我从小就很怕街上那些“疯子”,或者说,流浪汉。当有流浪汉从门前经过,我会吓得跑回屋里,躲起来。直到七岁(也许)那年,我用手里的石块和伙伴们一起战胜了自己的恐惧。我记得那个“疯子”没有落荒而逃,他还是慢慢地从我家门前走过,这让我们怒不可遏(尤其是当我们砸空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瘦瘦高高的,因为我从没见过瘦瘦高高的“疯子”,直到现在也没(也许是因为后来我长高了);然后当然是和所有“疯子”一样的脏灰色的略长的头发;接着就是一年四季都穿着的破烂军大衣,快四十度的夏天,他们都绝不暴露自己。我们当然没有像电视里演的熊孩子那样疯狂,也不是因为看不起他,我们单纯的是为了——取乐。为了在朋友面前显得自己勇敢。说实话,那时候我其实很怕他会发怒,会突然扑过来,因此砸的比别人少些,但又不至于明显到被他们发现。那时候我干的事儿像个畜生。
慢慢长大了,上学了,有点屁文化了,我知道了把他们叫作“疯子”是羞辱人的,并且开始像个真正醒悟的混蛋一样打心眼里同情他们。尽管我从没有用任何的行动表示过我的同情。“可我又能做什么呢?”看着流浪汉被人臭骂着赶走,我就这样欺骗自己,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一天我看到一个小个子的流浪汉,穿上了环卫的衣服,拖着比他还高的扫帚,跟着一个环卫大爷扫大街,环卫大爷用方言指责他扫的不正确,他就痴痴地笑,痴痴地跟着,好像落后一步,就会被整个世界甩开似的。从他们边上经过我是开心的,现在想起来也还是开心的,尽管我后来再也没看过他。
小时候有一次,晚上,我妈从锅里端出一碗粥来,她笑着对我说:“外面有个‘疯子’,你敢把这个端给他喝吗?”我连说不敢,吓得把家门都关上了。妈妈就对我说了一通他们多可怜的话,手里热气腾腾的碗,拉开门探出头去望了望,说:“唉,走远了。”我这才敢拉开门看一看,发现什么也看不清,街上路灯坏的,夜很黑,很黑 。
图片里的人在我家门前的水龙头装水喝,也是因为我妈心善。他几乎每天都来,比什么串门亲戚邻居,都频繁,我就想,要我认识认识他,我们都是最铁的哥们了。我只是自己跟自己开玩笑地想。只是想。可我妈还是会凶他:谁让你把水龙头开那么大的?以后不要来了!也会说一些脏话。我觉得他是什么都听不懂的,只看到那个曾默认他喝水的妇女在冲他吼,他就笑笑,好像眼前的画面有多好笑似的。我不知道我妈到底是心疼那点自来水,是嫌他影响买东西的顾客,还是为自己的善举感到羞耻(你知道的,人在嘻嘻哈哈的朋友面前,有时是会为自己的善举羞耻的)。有一天我准备洗手,发现水龙头的旋盖没了,我喊我妈,她说挂在边上的树枝上,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不给那个“疯子”用,让我洗完再放回去。我把旋盖安好,突然就不想洗了。
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21 00
21 00 - #21天写作挑战
我始终觉得小美人鱼的选角不是多恰当。
我很喜欢小美人鱼
第一次看,是在安徒生童话里
安徒生心理预设想必也是丹麦
我并不觉得选个角儿,选黑人就是平等了,就是宣传不歧视黑人了,就是种族多样性了
我觉得任何肤色是互不影响存在的
我觉得该尊重互相的肤色
黑人也要黑人的公主
如果说,把黑人公主牵强的换成白人
然后打着“不歧视白人”的平权旗号
也会很反感吧
这样不就是在自我民族不自信吗
不就是在自我民族否定吗
(什么都有设定)
小美人鱼白人是设定吧,我不觉得应该修改设定
至少尊重一下原著吧
以上我并不是在说肤色问题,而是设定和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做的问题
如果有一天一个黑人公主选角白人,我也会这么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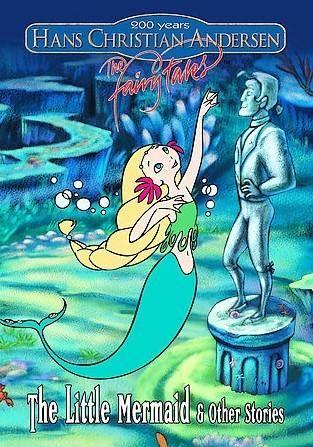 2 00
2 00 - #21天写作挑战 祁连遐想(三)
这次在写的这篇文,题目叫做祁连遐想,其实在之前更多的则是对祁连山,在我自己的视角下这短短二十年中所见所闻进行一些简单的记述。这并不是说我在写的文已经偏题。我过去看待祁连的视角和思路,就像是李白那首有名的诗“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是非常直观和简单的,即所谓“看山就是山”,看不到除了山以外的其他东西,因此在进行祁连山的描述的过程中,也只能将内心最为基础的那一部分写出来。真正开始以一种更为客观,或者说是更为全面的认识以及理解祁连山是在我大学之后了。
我一直有一个认识,即处在一个事件或者事物当中是不能完全的认识它的。这个观点也可以理解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并没有真正的从这座千百年矗立在那里的山脉中获得什么灵感。当我真的离开家乡,离开故土,走的很远很远的时候并且开始急切地思念家乡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它的壮美和巍峨。在大学的时候,跟同学介绍家乡我总要说起这座山,同时还要嘲笑一番南方同学家乡低矮的山峰,让他们好一番羡慕。这种骄傲感是自然而然的,是真正发自内心对于故土的自豪和自信。在我还没有踏出家乡的时候,听到过一些西北同学到东部求学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故乡的偏僻和落后而自卑的事情,这也让我在高三暑假很是惆怅了一番。但当我真正理解了故乡,并且爱上了故乡的时候,我相信我内心中,更多的肯定是自信和骄傲,在祁连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血液中自有来自高山的雄壮、来自大漠的直爽,也有戈壁中绿洲文化所带来独有的坚韧和爽朗,我深深为一个自己是一个河西人和祁连养育的子女而骄傲。都说云贵有十万大山,
今早走在西北边睡那座小城沿山而建的那座柏油路上,一路颠簸一路俯仰,那深蓝色磐石之上的雪峰——这祁连岂止十万大山?小时候跟所有的孩子一样,好奇在山的那边到到底有什么。但是到真的知道之后,反而不敢相信,这山的那边就是世界的屋脊青藏高原,原来我跟那传说中的地方,只有一山之隔。
如今眺望祁连的时候,早已不能像小时候那样细细去数山脚下到底有几个小镇。小时候的看向远方的目光都很清澈,很清澈。如今看向故乡的眼光,却很深远,很深远。 6 43
6 43 - #21天写作挑战
Day3
昨天白天喝了星爸爸 晚上兴奋到三点终于迷迷糊糊睡了
五点被雨棚漏水滴醒 无比卑微的给老板请假补觉
暴雨成都穿着大短裤卫衣拖鞋出门 回头率之高
和小姐妹去吃了串串逛了校园 发现阿姨为别的女人拉起了横幅 唉
分手第三天 要说完全不难过也不可能 在厨房边台上看见郫县豆瓣差点哭出来 他也想过做饭给我吃的啊 倒是最后一顿饭一口也没有吃到 唉 就这样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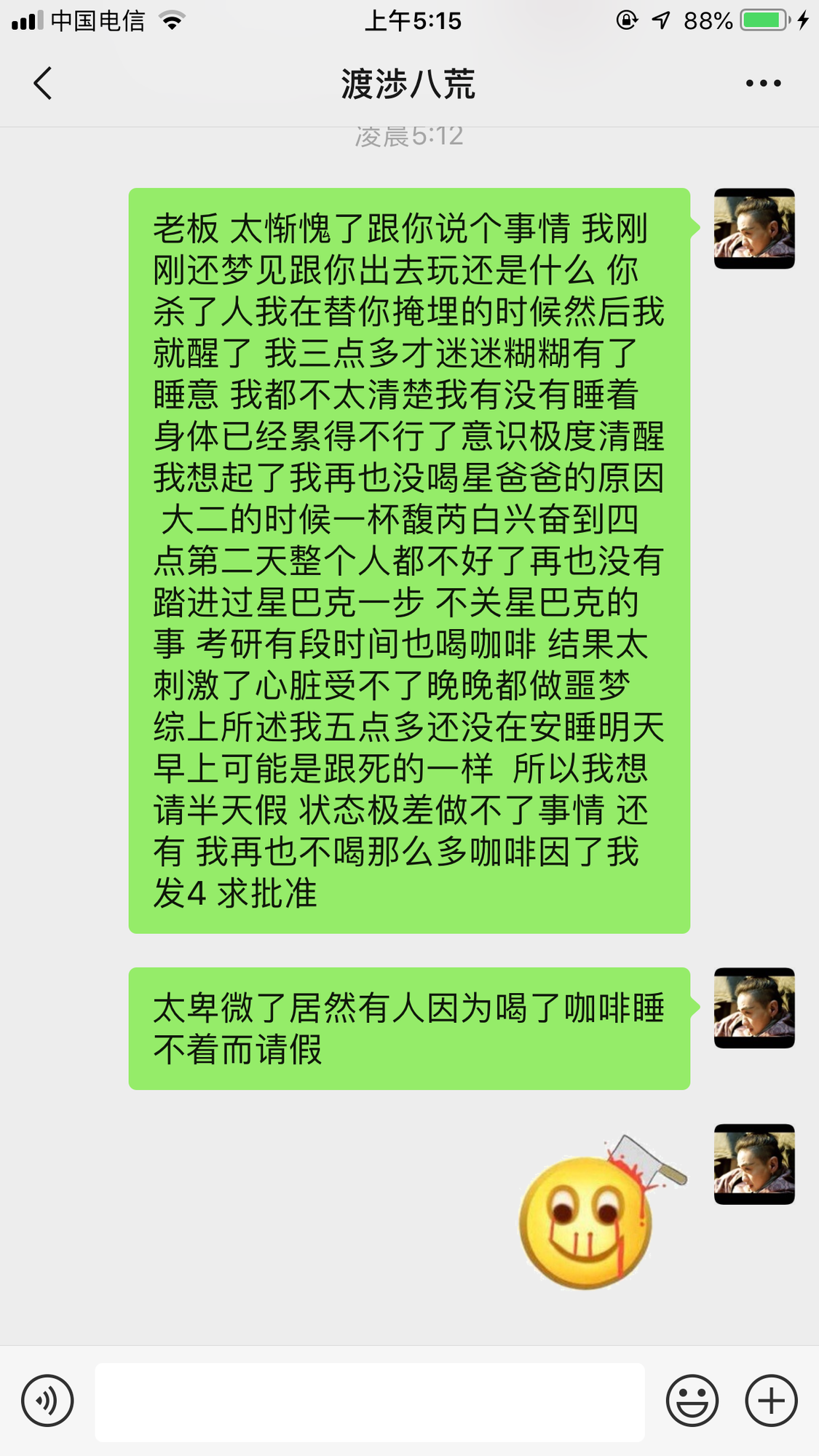

 4 50
4 50 - #21天写作挑战 Day04“观念如何演变”
观念的演变往往不是像我们常规所想的那般连续平缓,一个世代一个世代人不断成为着社会的“地球之盐”,成为足以推动社会理念变革的主心骨。今天和我妈讨论了一下,我说我有两个足够肯定的未来方向,一是不会留在家里,二是越晚结婚越好。第一点是因为实在足够厌恶小城市的人情网络,第二点是因为,我要确保我拥有足够的能力保证两个人的快乐满足的生活之后,并且能够给予下一代安全良好的教育环境后,我才愿意结婚,从现阶段的自身能力和社会环境来看,实在难以满足。我妈还算包容理解,但我说得非常极端,我说你们一副为了孩子孩子操劳一生的样子并不显得有爱,我愿意满足自己让自己快乐也没什么错,如果可能我甚至不愿意结婚,观念的不同罢了。我说这个不是想证明自己的观点有多正确,我想说的是这种观念的演变的难处所在,之前看过一场一席的演讲,提到一个观点:在中国最最需要女权主义思想的是如今那批四五十的中年男人,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因为这批人是现阶段掌管社会的家伙,倘若他们非常油腻地在ktv找着女招待,为什么主义者们不去好好批斗一番呢?因为惹不起的,但恰恰改变他们的观念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是现阶段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和掌握者。褪去少年莽撞之后我发现我仍旧讨厌着现阶段这个社会上的中年群体,更讨厌那些刻意迎合,少年老成的年轻人。都说历史螺旋形上升,我们这一代学习拥有的新潮玩意最多,希望这届青年能少些螺旋,多些上升,别屈服得太快。13 10 - #21天写作挑战 少年看多了姑娘,觉得热觉得渴,想去路边买水。他停了自行车,靠在路边杂货店。就在这掏钱的功夫,一转身发现自行车被骑走了。杂货店老板问,你这车不是共享的啊?少年摇摇头。杂货店老板从柜台里走出来,又问,外地人?
少年点点头。
杂货店老板从上到下打量了少年,盯着三只眼问,刚来的?三只眼都能看见?
少年点点头。
“我这儿没监控,一年到头亏不少钱。你车也被骑走了,留我这儿看看店。要是哪天你乏了,再有人路过停自行车买水,你也给他骑走呗。”
“我吃啥你吃啥,晚上关店了你在我这儿睡。一个月管你一顿酒,这店门口,我还署你名字,干么?”5 00 - 我很喜欢那个爱和恨都大大咧咧的基友。
我曾经老是想,他想的没有我丰富,没有我周到,甚至做的事情无一例外的都在说明,他是个没有经历过多少思考的任性的人。
我不应该有办法他好好做朋友的。
但是很妙的,
我们这种孤僻的人总会有在孤僻的地方,有一些奇怪的共鸣。
即使我们甚至有一段时间觉得会老死不相往来。也因为没有办法回想起来的原因,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我自以为是的厉害,他无从感知。而他那些我从未做到的坦荡自然,也让我相形见绌。
交朋友,没用到办法,就是聊天就聊到了。
总是和对别人的样子不那么一样,
可要说为什么,我又给不出范式了。
我也不知道。
不过好像也没必要知道。哈哈。
#21天写作挑战2 00 - #21天写作挑战
【三明治编辑推荐内容·第四辑】
第四天了,不知道坚持写作打卡的即友有什么感受?话题里有随性的流水日记,也有认真构思的写作练习。这更多是一种寂寞的坚持。不像段子和视频那么热闹,那么容易吸引人的视线。但写出来你会明白文字的重量,它能承载你的多少思绪和记忆。
没被推荐到的小伙伴不要着急,还有那么多天呢。当然如果有自己觉得写得比较满意的,可以艾特我,会来仔细看的。
@Hysterin 今天第一篇推荐是关于为什么参加写作挑战,说到心坎里了。这个时代要坚持写点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太难得。能找回少年心气是件美好的事。不妥协的态度,很霸气。
@饭桶君 有趣的人物观察,小区楼下与城管打游击的卖麻辣烫的阿姨,寻常的生活细节里呈现出一种真实的幸福感,转瞬即逝的画面被文字定格下来。
@我不是奶酪 关于奥兹海默症,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残忍的病症,但在这些具体而微的人物和细节里才真正明白,家人有多难受。
@海马先森 从给实习生租房想到了很多,大概因为作者从事行业的关系能讲出很多真实的现象。不同职业视角的观察也是我们感兴趣的内容。
@daydayup_up 很有镜头感和画面感的描写,像一副安静的油画。结尾写得好,“好像只有从重复的日常里抽离出来,才有这样的心情,想好好地抬头,看一看星星。”
@兰二一 一道煎豆腐,写出了很多记忆里的故事片段。用一元纸币或钢镚儿装回来七块豆腐。细节到位,自然能勾起共情。
@即友_9BJRP0 写中二这个题目写得很妙的一篇,画面感挺强,语感也不错,中二少年的心境跃然纸上。
@海期浪行 推荐这篇是有两个场景触到了我,一是关于爷爷的,灰烬飞向天空勾起无限遐想,二是关于那片无尽的黑暗。很难描述的感觉,但人们总是尝试着去接近它,以读懂生命存在的意义。
@没有昵称的小透明 小时候总会很认真地去做一些幼稚的事,但想想还挺可爱的。就像第一篇推荐里的作者所说,那时没有功利,充满热忱。或许我们需要时不时回过头,去拾起那样的初心。
一起加油吧
昨日回顾:m.okjike.com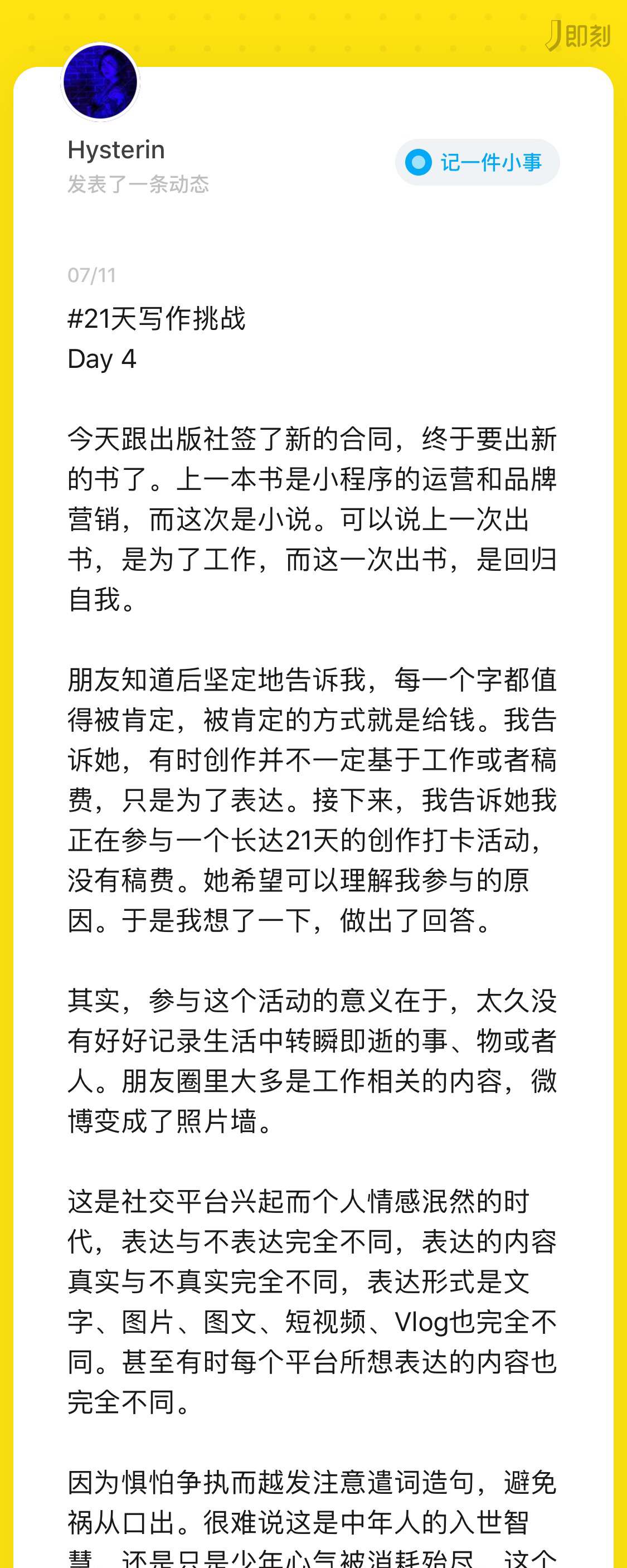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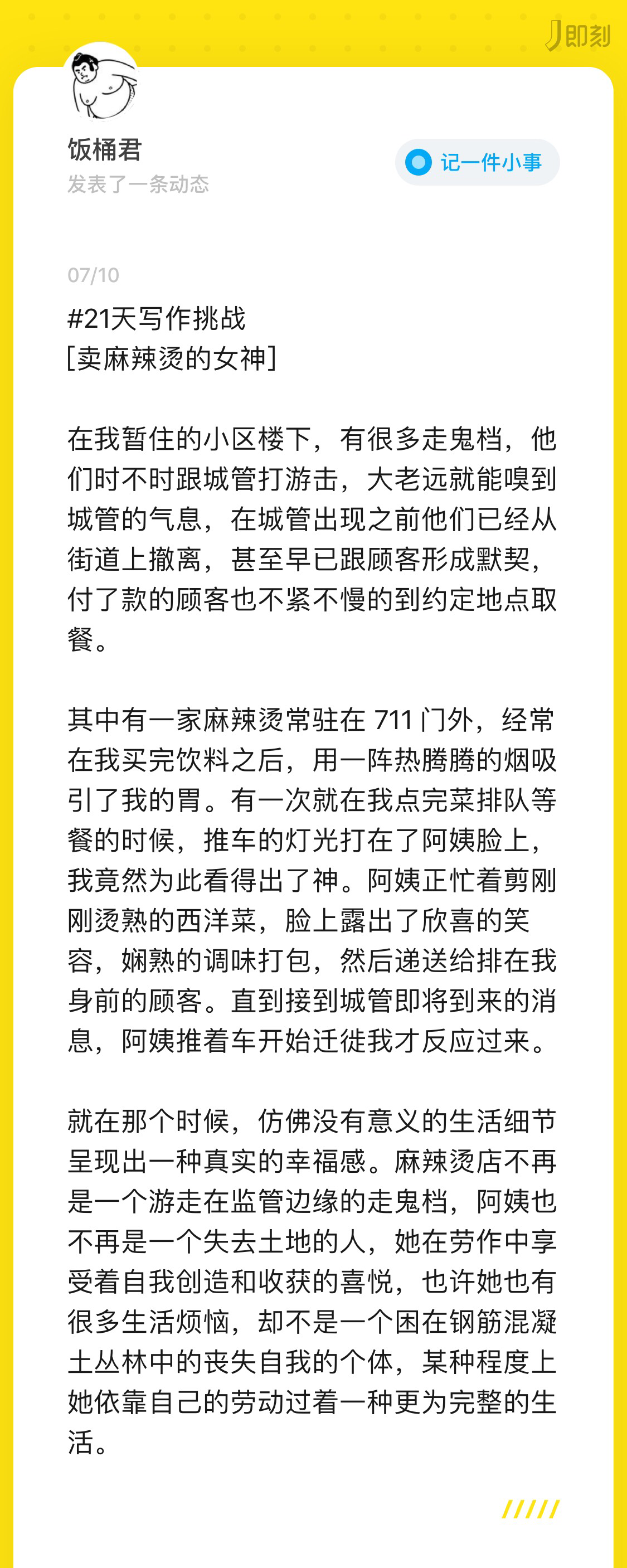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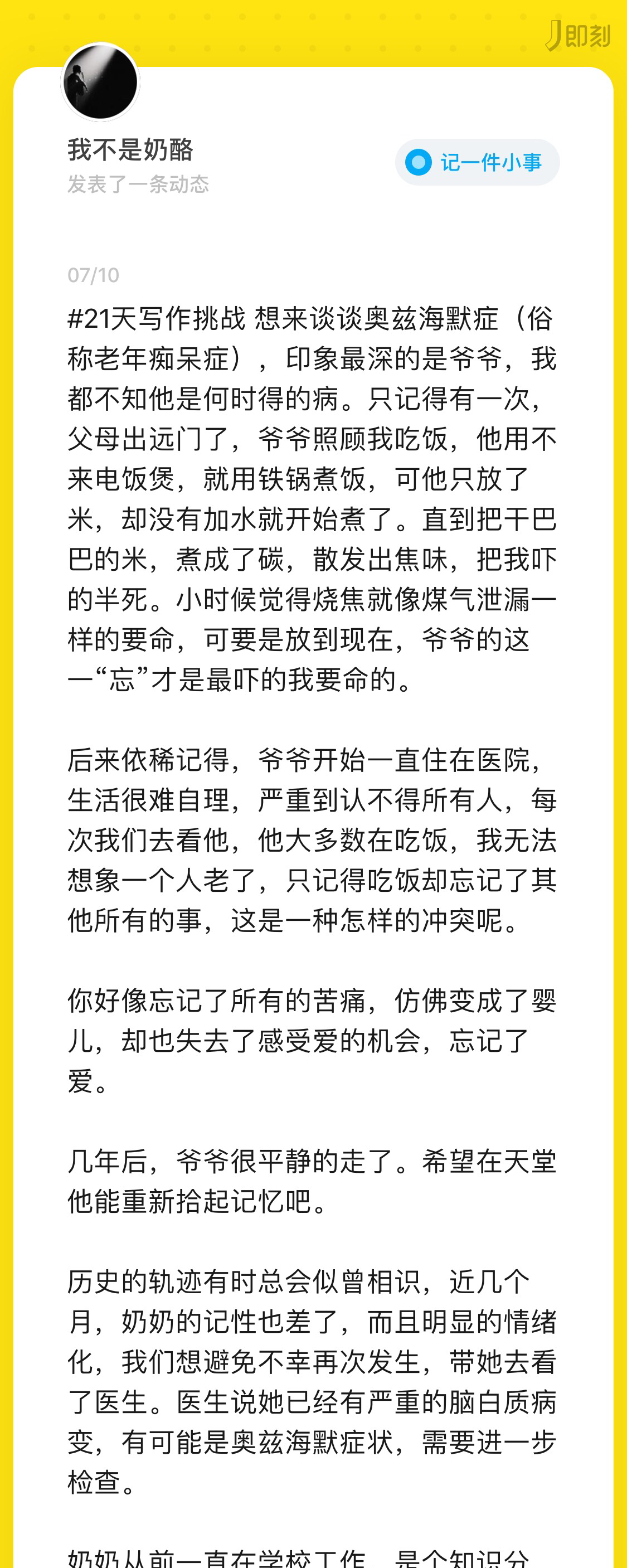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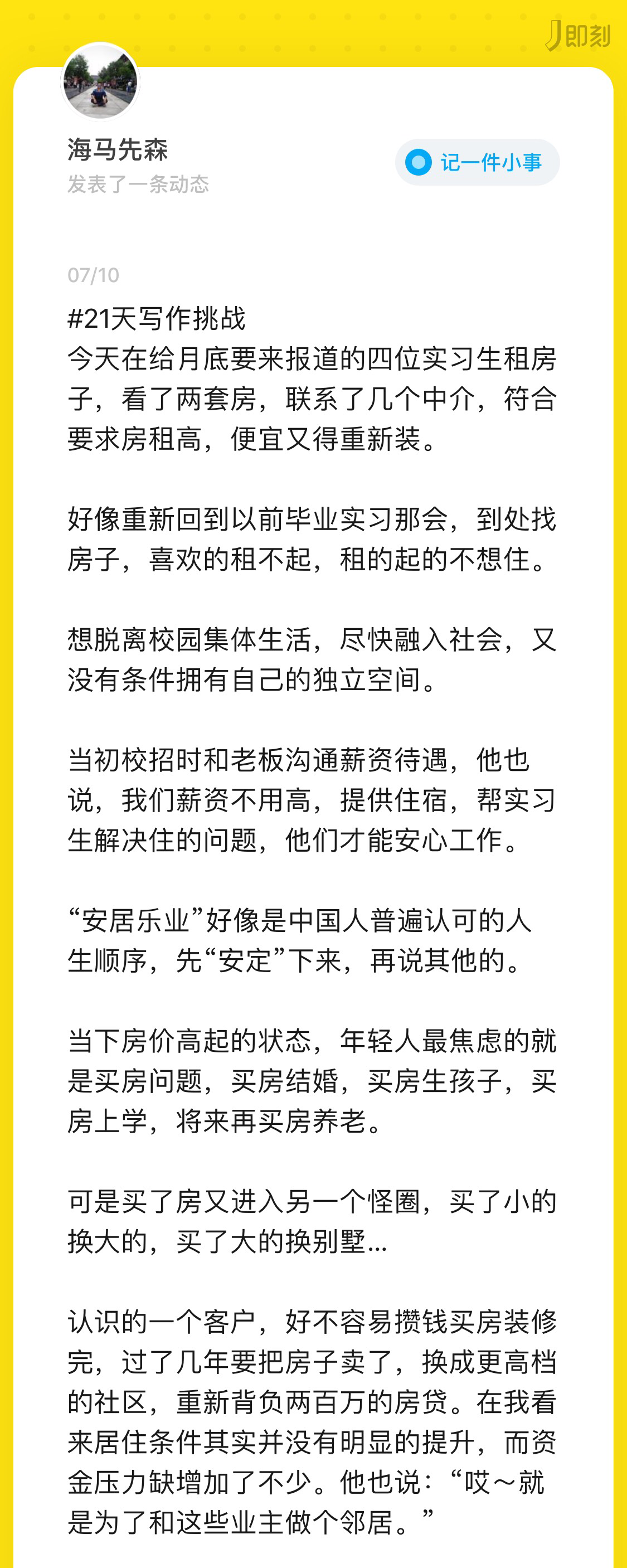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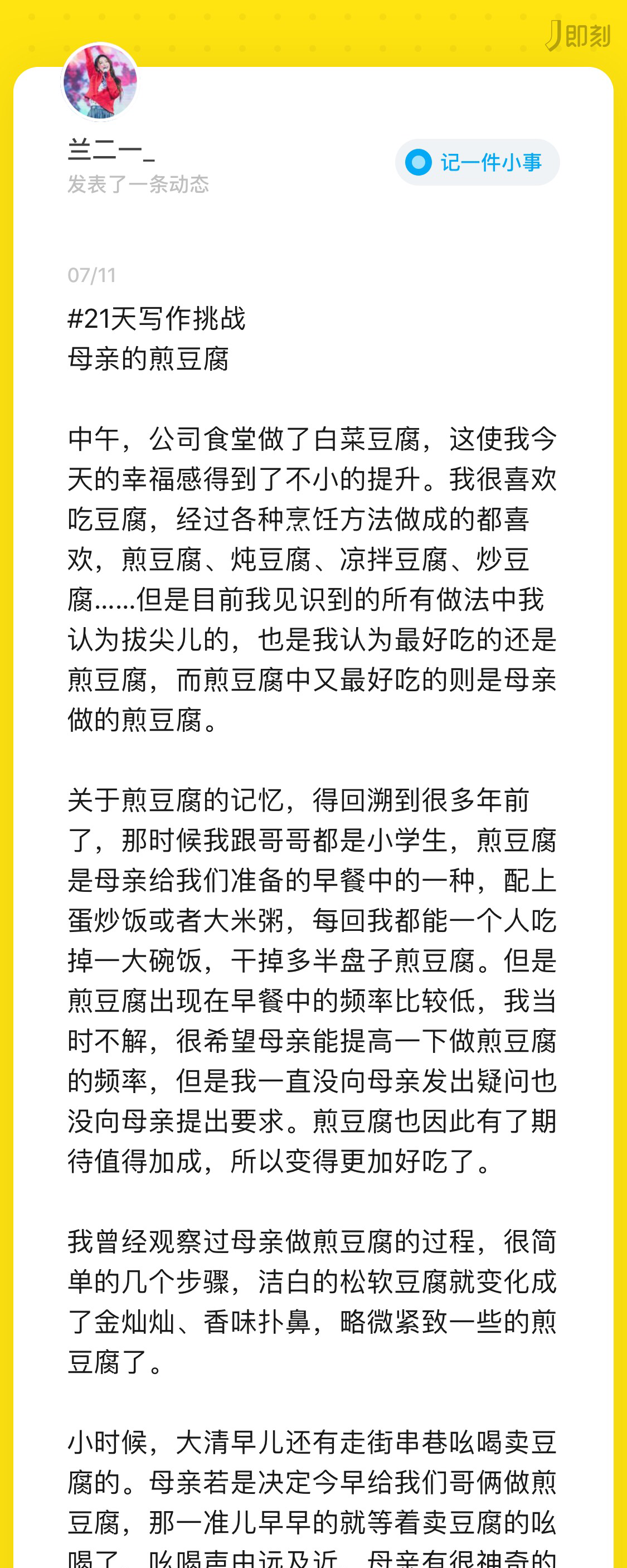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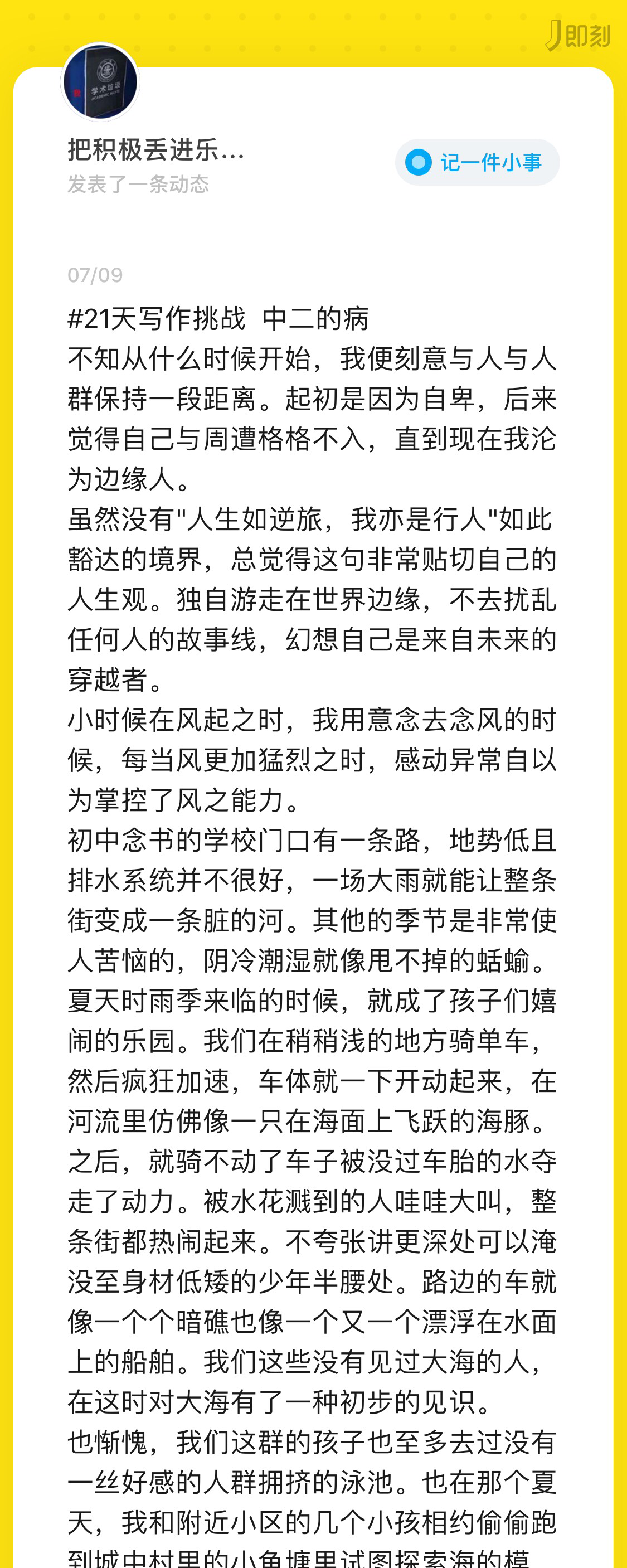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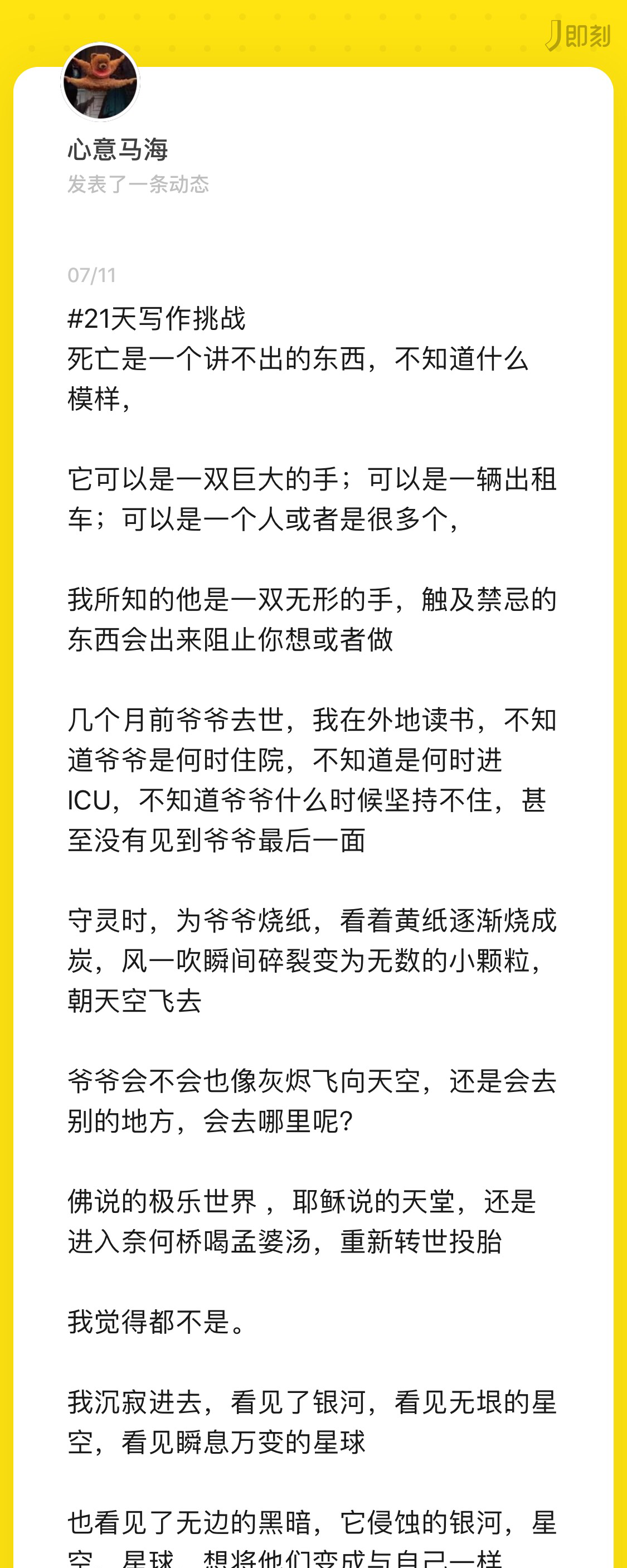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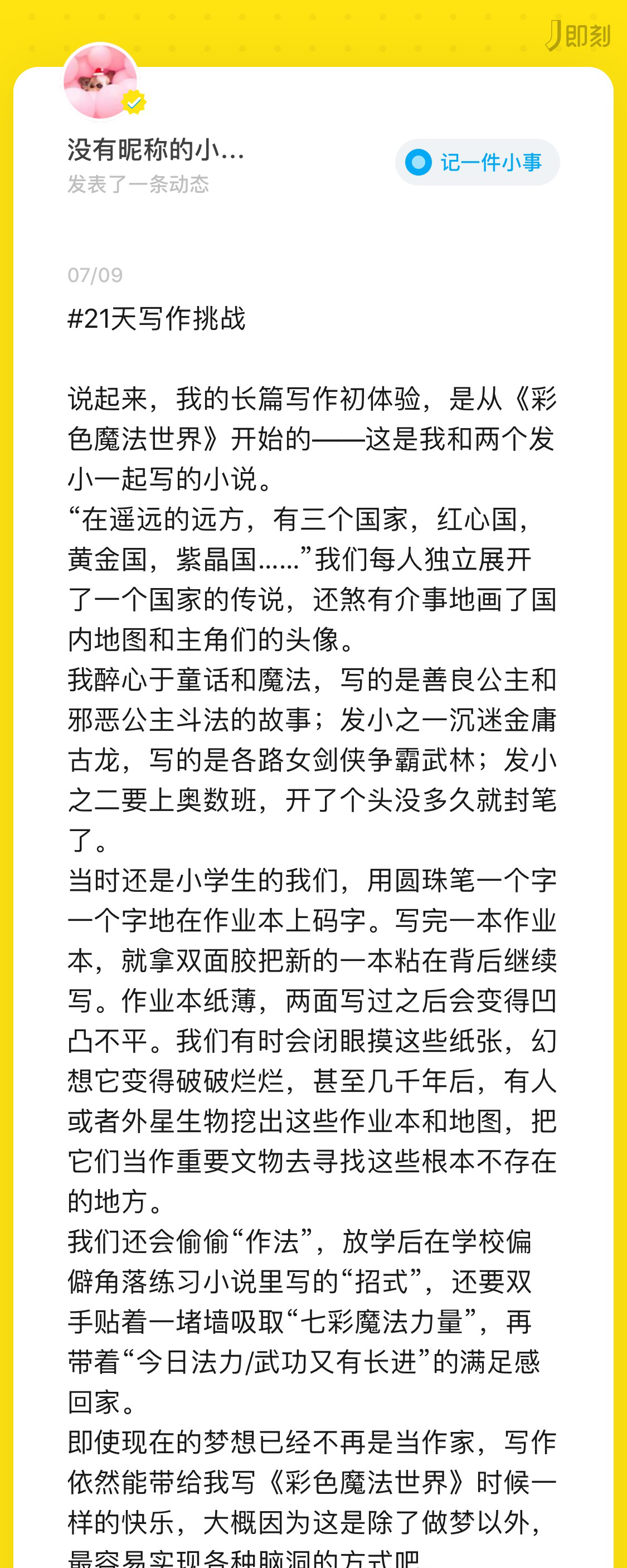 26 143
26 143 - #21天写作挑战
《不行,得加倍!》
有时候我在想,我能不能在路上捡到一张中了一等奖的彩票。可是转念一想,一等奖最多才1000万,够我挥霍一辈子吗?
不行,得加倍!
可是要是原主知道我中了奖之后找上门怎么办?那样还不得把奖金交出去。不行,我捡到了也有份儿,你至少得分我一部分才行。可是这样的话钱就不够分了呀!
不行,得加倍!
如果能中5个亿,就算分给我1/10也有5000万,足够我挥霍一辈子了。可是如果原主不同意怎么办?那就打官司吧,好歹是我捡到的,花再多的钱这个官司也要打,可是这一部分钱不应该算在现在我的头上吧?嗯,把它算在未来分到的那一部分里吧。
不行,得加倍!
要是中10个亿。还不愿意分给小小的几千万给我,那就鱼死网破好了,反正彩票在我手里,谁也别想得到它!要不是我捡到了,指不定就没了呢!中了这么大的奖还这么吝啬,活该丢了!可恶,真是越想越气!我……
“你在干嘛?”2 10 - #21天写作挑战
【忘不了的故事】
昨天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在小组任务里,听了组里其他三个人讲了他们各自的一个故事。他们都是乡村的一线教师,年纪三四十岁不等,来自的地方也不一样。
他们与我都是第一次见面。本来只是要求随便讲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但他们的故事好像都是从贴着心很近的地方拿出来的,我听完之后也跟着忘不了了。
第一个讲故事的人是一个大叔,长相酷似韩国演员柳海镇,就是那种最普通的在地里挥汗如雨做农活的男人模样。他讲他小时候跟着叔叔到镇里去,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馒头,很甜很甜,”原来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啊”,他边讲边用手形容,好像回到了当时无比雀跃又小心翼翼的样子。就在我好奇那个好甜的馒头究竟是什么好吃的的时候,他接着说道,“后来过了好久,我才知道那个东西叫面包”。
第二个讲故事的是一位大姐,她说起当年上师范学校时的事情。从家里到学校要乘坐的车本来是人坐满了才会开的,但是那天车上只有她一个乘客,车就开走了。然后当她抵达学校,前脚刚进宿舍,后脚就听见有人敲门,竟然是爸爸。当年没有手机,她爸爸知道了车上只有她一个乘客之后,担心她会出什么意外,就马上放下自己手中的事儿,跟着转了几次车跟到了学校,亲眼看她安全了才放心。她本来要留爸爸一起在学校吃午饭,但爸爸要回去忙事情急匆匆就走了,她说在学校门口看见爸爸的背影和许多人的身影混在一起,自己的眼泪流下来,朱自清的那篇《背景》她终于懂了。
还有一个小姐姐,也讲了她和爸爸的故事。高考的时候在考场附近租房,只有一个房间,爸爸还非要和她一起去住,她是很嫌弃的,因为觉得自己都是那么大的姑娘了。可是后来发现房间里有蚊子,她的爸爸突然穿着背心大字张开躺在床上,她问爸爸干嘛,爸爸说,“让蚊子都来咬我吧”。3 21 - #21天写作挑战
火车上突然想起我爸。
我爸总喜欢揶揄呵斥我们娘俩,把我的坏毛病一股脑全推到我妈身上,我妈没少因为这受过气。可能是我高中选的不够好,我妈下岗,家里的支柱就是我家老头子一个人,受累太多,年近半百发的牢骚是越来越多。有时候听着他数落我妈,我常皱眉头,总是想和他大吵一架。
他也很爱我,说实话,我花钱老是大手大脚的,不太像一个……穷苦人家。但我爸从来没说过什么,电话里总是问我缺不缺钱,好像我要多少他就能给多少;小的时候我想吃雪糕,我妈不让,他就偷偷买了两根,我一根他一根两个人躲在阳台挤眉弄眼地吃完了;视频通话的时候,总是自己霸占着摄像头,把我妈挤到旁边。我妈接我话茬的时候他就白眼一翻,怨我妈挤占了他和我聊天的时间;可真和我聊的时候又总是容易扯远,文不对题离题千里地说一大串。自己又觉得不满意,那几句话又反反复复说上几遍才行。这时候我是不会感觉烦的,他太可爱了。嘴硬心软让人忍俊不禁。
就说到这里吧,有些东西还没准备好该怎么说。虽然说了一些他老人家的坏话,但终究还是爱比恨多。希望我以后有能力做一个能照顾他的人,就像我小的时候他对我那样子。3 20 - #21天写作挑战
【昨日黄·我的成长回忆】
4.中二青春
中二是神马
中二就是相信喜欢谁就直接告诉他
中二就是晚上刷夜觉得特别酷
中二就是信誓旦旦觉得自己可以成为诗人
中二就是天马行空的没有约束
中二就是不念未来 未来自有安排
中二就是不喜欢的人就断然拒绝
青春很近又很远,尝试了很多,并没有遗憾吧,反正也没法在重来一遍.
有些对,有些错,但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无法左右和改变吧
5.初恋这件小事
6.我的童年阴影
7.追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13 10 - #21天写作挑战
今天坐火车回老家,真的是!一坐火车我就晕车,像被人打晕了一样。我们卧铺对面是一个家长带着两个小朋友,我家小猴子一上车就和他们热情的打了招呼,我也赶紧找好角落蜗好。(:3_ヽ)_
我们是后上车,对面已经吃起了零食,我们家小猴子那直勾勾的眼神哦,人家马上把酸奶分给我们一份。一会儿对面家长问自己的孩子吃不吃糖果,结果被我们家的抢答了,自然又有了我们一份。后来对面小朋友从自己小背包里拿出一个小瓶子,我家崽子就问了一句,“姐姐,瓶子里是什么?”人家就马上把东西放在你手上…
我觉得这样吃别人家的东西,挺不礼貌的。只是每次拒绝的话刚说了一半,吃的就已经递了过来,接与不接呢?哎~实在是太客气了。_(´ཀ`」 ∠)__49 80 - #21天写作挑战 第四天
放假了,回到我亲爱的家。见到我亲爱的小伙伴儿。我这就毕业啦。
我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学到就毕业了。真是虚度光阴的好例子,啊,我的老天爷啊!我还想做咸鱼啊!
但是作为一个咸鱼,也是要翻翻身的,明天儿就要好好努力找工作。成为一个称职的社畜!!好好的按时下班!(真的可以吗?)2 00 - #21天写作挑战 蜗牛
☞我要一步一步慢慢爬。不慌不乱,不紧不慢。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活广州。
深夜,街头,蜗牛。
☞小孩,两个男孩。好奇,不敢靠近。
他们虽说怕,但还是凑近看了又看~
一个问,它会咬人吗?
另一个答,要不,你伸手试一试?
两个人相视一笑,好有默契!!!
☞我猎奇,蹲下拍一张。然后直接转身就走。
很久没有看到蜗牛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印象中的蜗牛好小一只的。怎么今天偶遇的这只会这么大??或许???品种问题???不清楚!!但真的炒鸡无敌大只耶~
想起来周杰伦的歌☞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积极,向上,让人挺完充满力量~
或许,过了充满童趣的时候,已经不会跟别人分享看到的一切有趣的事或者物~因为,很少人会get到你的点~可能⑧,时间节点真的很重要~
☞有感而发
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折,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地去改变,找到一个平衡点。跟世界相处,首先是和自己相处。天黑开盏灯,落雨带把伞,想念就见面。很多时候,来不及只是一个借口,是一个对你自己来说很善意的谎言。
所以,请看淡你所觉得特别特别特别让你气愤的⑧,或许这才是人生~❤
 9 20
9 20 - #21天写作挑战 第四天:天府之国第一天
趁着《千与千寻》的热度,一路伴着宫崎骏的电影来到成都。电影里天马行空的想象完全不会给人荒诞感,因为那些妖怪都单纯如一个孩子,多洛洛会因雨滴到伞上的声音而兴奋不已,波妞因为宗介无意间的救命之恩而死心塌地。绝美的画面配上淡淡的情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浓郁渲染的哭笑,仅仅只是一个孩子的大笑,便让人忍俊不禁。宫崎骏电影中让人心驰神往的不仅仅只是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更多的还是人与人之间那令人向往的相处方式。
由于到成都已近晚上6点,于是成都之旅自然就从火锅开始。鲜是真的鲜,然而无福消受啊。开始还没觉得辣,但每一样菜尝下来,便不能再多夹一筷子,开始猛喝茶,偷偷抹汗了。
另外还有一点深刻感受,仅仅到这个城市几个小时,我发现四川话便深深刻在这座城市里,无论走到什么场合什么人,都能听到抑扬顿挫的四川话。我说四川对外乡人真不友好,却又禁不住羡慕这浮在城市空气中的浓浓氛围,大概这就是文化吧。
至于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莫名害怕某种不期而遇 人也好事也罢 总归是些芝麻陈谷子烂事 3 20
3 20 - #21天写作挑战
今年夏天我毕业了
还依稀记得2015年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蹦蹦跳跳无敌开心的和男朋友和老爸说我可以上本科了
当时的蝉鸣也和现在一样,吵闹无比,混着家犬的狗吠声和麻雀燕子的叽喳声
后来,和男朋友一起录取了桂林的大学,我们两的学校只有一墙之隔,放假时间也是同步的。
所以我们每逢法定节假日就要去周边城市旅游,从桂林阳朔、南宁青秀山、长沙世界之窗、广州小蛮腰、深圳红树林等等,以后还想和他去更多地方,经历不同的四季
在学校的这四年,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大二的时候和一个舍友吵架了,因为一些误会。
这个矛盾一直持续了两个学期,一整年,虽然最后和好了,但关系和感情再也回不去了。
还记得,那段时间不喜欢待在寝室,就经常在自习室和图书馆待一整天,因此考上了英语四级和计算机二级(我学习真是不太行,大学就考了这两个证)
也是那段时间我爱上了长跑,热爱那种忍耐过后焕然一新的自己
现在
认真对待身边的人和物,就是我最想要学习的事情
最后,表白石原,希望能成为和她一样认真爱自己,独立自主勇敢坚强的女性 3 10
3 10 - #21天写作挑战 此去别后,我已不愿相见
“最近怎么样呢?”我轻轻碰了她一下。“你好像有点心不在焉……”
“嗯。”她的声音很小,我仿佛看见一个黑暗中瑟瑟发抖的孩子。
“最近一直在颓……”我没有看见她的眼睛,她也没有看我。“我妈妈要让我学别的。”这令我稍微吃惊,听她的声音也是没有颤抖的感觉,很平静。我似乎浅尝了一片苦瓜,苦涩浸润了嘴角。
我已哑然,但还是说了些话。
“可能,会更好吧……”
“我不知道……”她的声音很安静,如无风自动的落叶。
我回去了,想着,也该做点什么……毕竟,我不明白这种感觉。
于是,我发了两条短信。真的奇怪,我竟等着手机的反应。
还有十多分钟,我就必须就寝了,但她没有回复我。我多么希望听到那清脆的响声,即使哀怨也罢了。但什么也没有,她,没看见,睡了,又或者,我心中也有了些答案。
她来了电话,我慌乱地推了推被子,埋怨自己为什么爬上了床,为什么不直接接了电话。等我下了床,电话已经挂了。
没有多想,我忙回拨回去。我知道,没人安慰的失落有多么可怕。电话,接通了。
“我妈妈……已经……她和老师说好了……”她在掩着颤音。那么,这就是真的了,也已是定局了吧。回想她遥望梦想时的,有点卑微的笑脸,我不禁有些悲哀。
而我,不能说什么,没有能力,更没有那种被人推崇至极的勇气。
“学吧,应该会更好的,你可以先试一试的……”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并不能预知未来。
“嗯……”
走廊的风有点凉,天上的云要压下来。
风和日丽的天气,就那么几日,阴雨绵绵的日子怕是又来了。
后来,我们没了什么联系。她的未来,在我过去不想干涉时,就不再打算出现。
还有很多人,还有另一个三年相处的女孩,他们,都想向我走近一步。
我从不摘下面具,因为他们不是能看见我全部面目的人。
说实话,我有一种骨子里的自卑,他们不曾离去,我却想着遁入人群离去。 2 00
2 00 - #21天写作挑战
下雨的一天,早起追完了晚上没有追完的长安十二时辰,顺便出去走了一圈,梦里立的Flag今早照旧不管用,日子天天过,肚子渐渐圆,理想总是那么美好,现实总是那么臃肿,山大学伴引起了网友热议,社会原来真的像雨天那样不黑不白,只是灰。 2 00
2 00 - #21天写作挑战 你不知道痛苦和快乐哪个先来临,就像今天即刻无限期停用,就像我以后的每一天都点不开我为数不多的乐趣。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着即刻回来的那一天,我不知道还要多久。还要多久我才能见到这些素未谋面但却面熟的不行的即友们。怪舍不得的。分别总是痛苦的,但是我知道我们还会再见的。
后会有期各位(ฅ>ω<*ฅ) 7 20
7 20 - #21天写作挑战
剧本游戏📖
和几个陌生人一起玩剧本《惠子》,没有我想象中的精美人物服饰和场景模拟,几瓶矿泉水和咪咪虾条构成了这个午后。
我👉典型的唯物主义者,不喜欢鬼片、鬼魂、笔仙碟仙之类的……
也不知道逻辑推理能力很弱的我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辩论、剧本游戏这些费脑项目🤔

 4 00
4 00 - #21天写作挑战
早上朋友圈一姐姐分享给我一个文“不想结婚 有错么
事情都有两面性
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卵用 改变不了当下的任何境况
你看了这些文 还是要活在当下 依旧没有对象 依旧被别人说三道四 你自己依旧在承受这一些
有什么用 根本就没有什么方法论
没有方法论的建议都是空想主义
不必说5 00 - 下午坐公交的時候站在了後門的位置,靠站時隔壁上了個小學生小胖,他隔著關著的車門跟車站的朋友道別,很賣力地揮著手,嘴上喊著下學期再見啊!車駛出了站,他也還在揮著喊著。車再駛遠點,他往車門靠了靠,還在揮著喊著。#21天写作挑战5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