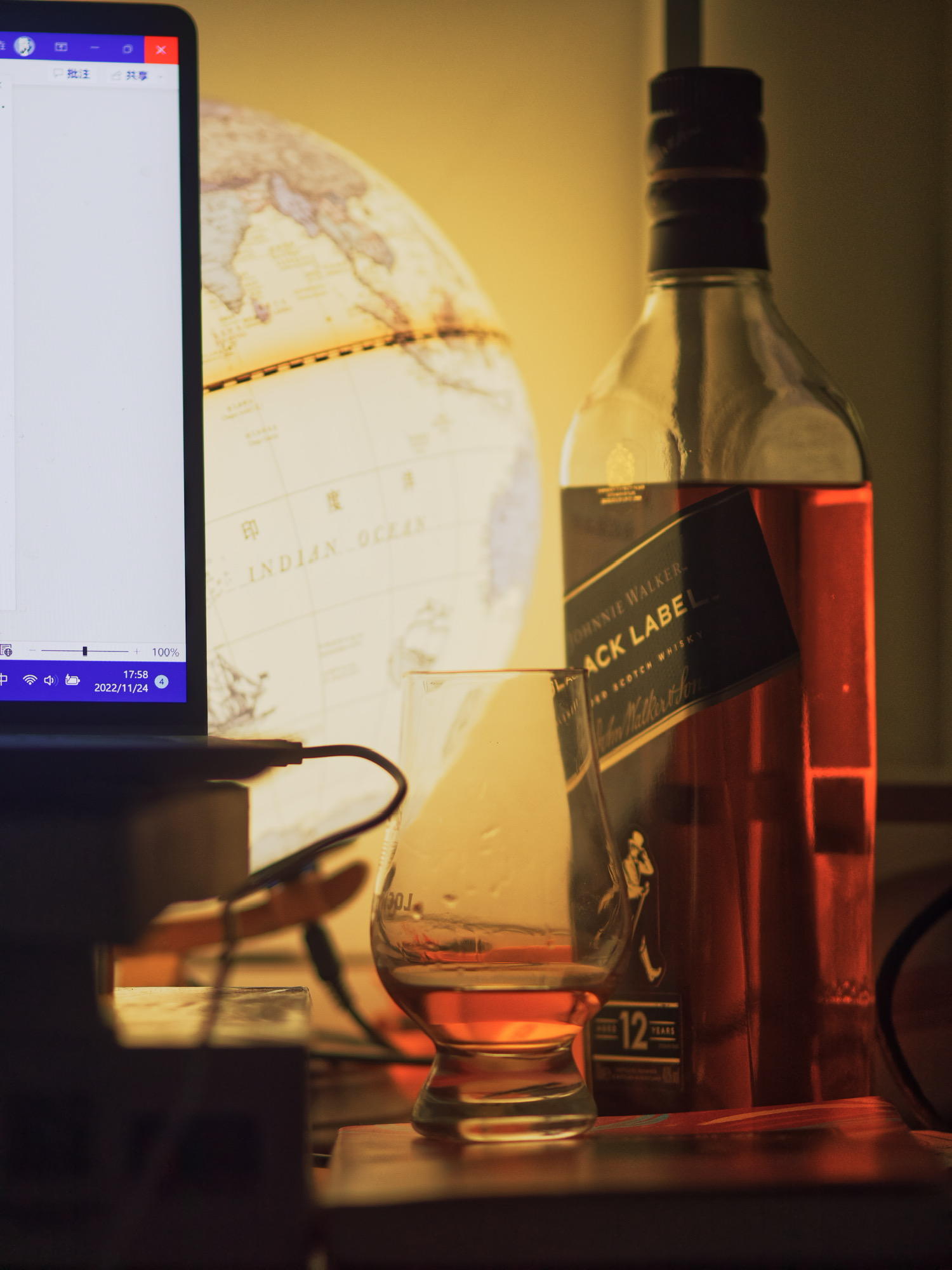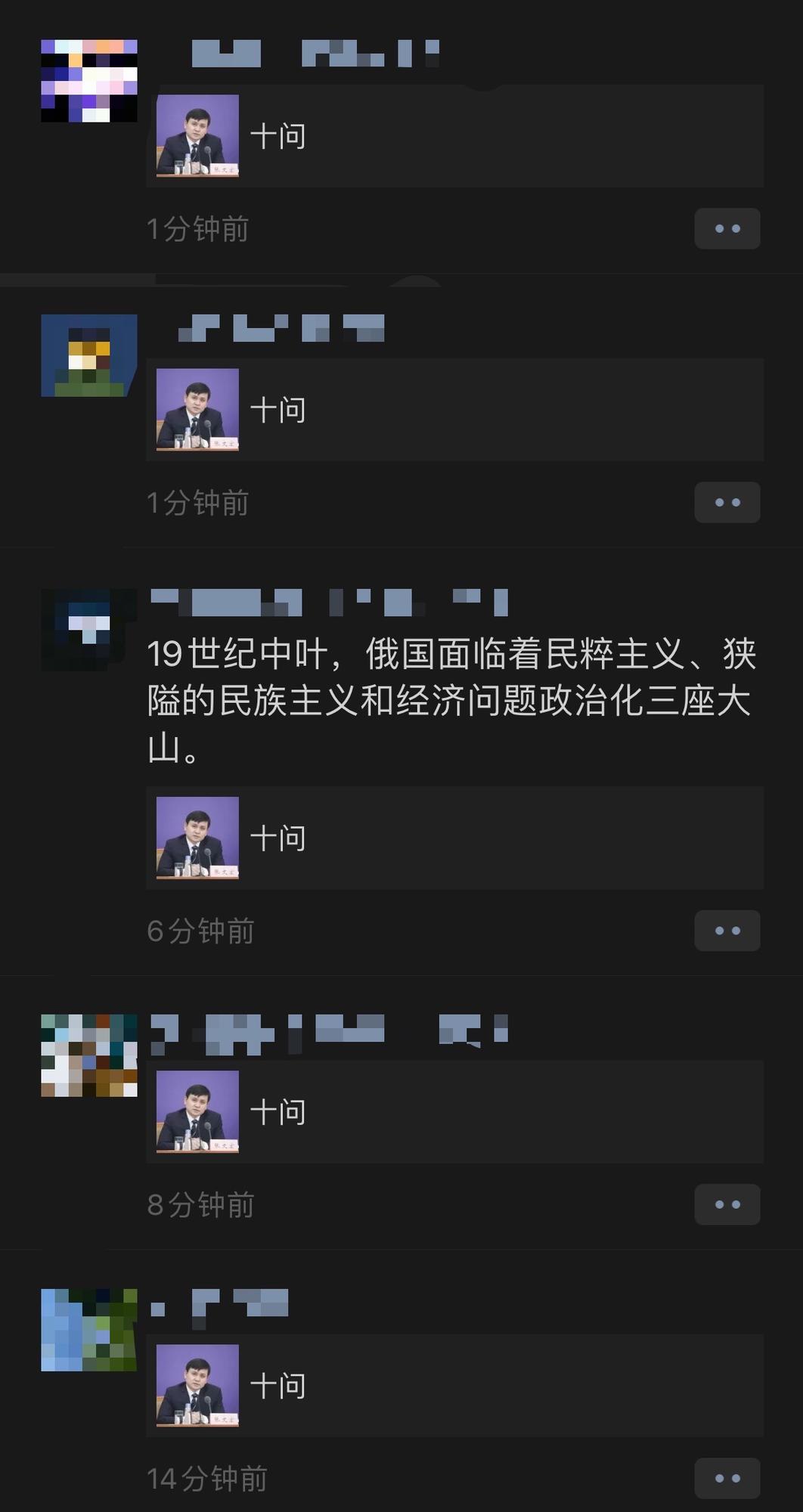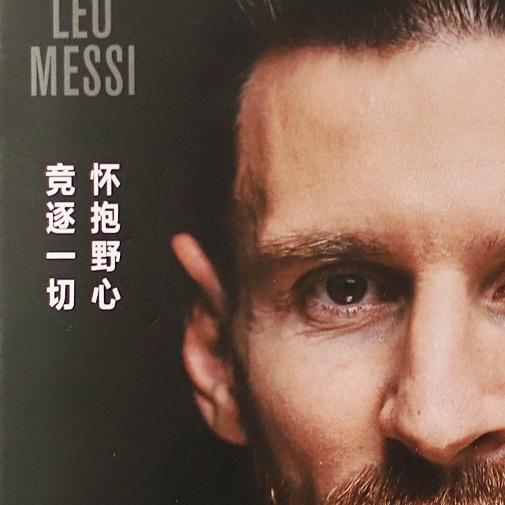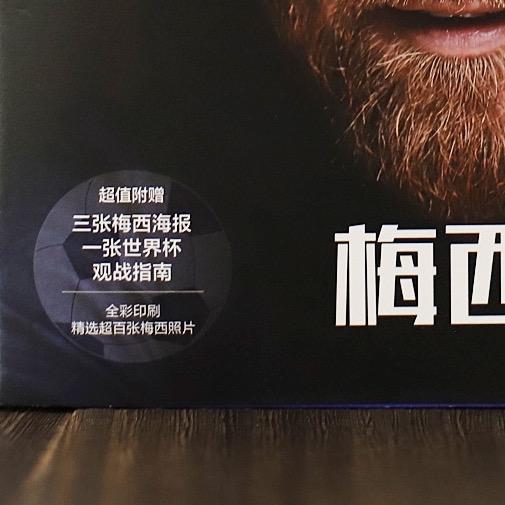即刻App年轻人的同好社区
下载
挺害怕自己十几年后变成这样——对别人随意指手画脚、以为成功学就是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充满好为人师的油腻爹味不自知、拿着空虚刻奇媚俗还自以为高雅的照片打油诗和昵称装点社交形象的中年男人 //@冷月清辉: 评论审核中

漏气妇女: 在南宁见了高中玩得最好的两个同学。 A在高校行政岗,B在税务局。 要不我们仨能玩到一块呢? A的领导让她竞聘科长,她找了一堆说辞说自己不符合条件,没去竞选。 我问升职不是能涨薪吗? A说:“但我还想要命啊,我还想要生活啊,我想要周末有时间骑车、去江边喝咖啡啊。不然你下次再来,我就没空陪你玩了啊。” B高中时作文就写得好,在公家单位也很容易受欢迎,领导多次给她一些评比、展示的机会,也被她以孩子还小,不方便为由婉拒了。 “其实我回家啥也不干,就往那一躺,婆婆和我老公照顾孩子。” “我就喜欢现在规律的工作,做完自己的事就下班,谁也叫不动我干别的。”
9 100
这个号停用很久啦
欢迎大家关注曾经的小号@七土
欢迎大家关注曾经的小号@七土
12 50
4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