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刻App年轻人的同好社区
下载
读Bottle of lies的过程中,反复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一切真的都糟透了吗?
印度仿制药公司兰伯西前员工萨库尔在2005年就向美国FDA举报了这家药企的造假行为并提供证据,但直到2013年,才终于进行了法庭听证,最后只不过是达成和解(赔钱了事),没有任何人需要负刑事责任。
8年,在一个人一生中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得到的还是这种结果。
美国FDA某任国际药物质量部部长说,“我这个人喜欢祈祷。但是某个批次的药是好药,不该成为我们祈祷的内容。”
如果监管不到位,普通人又能寄希望于什么呢,祈祷?
跟ChatGPT交流了一番,它说:
现代社会并不是靠“所有产品都可靠”运行的,而是靠“出问题的概率被控制在大多数人尚可承受的范围内”运行的。
我仔细品味这句话。好吧,欢迎来到现实世界大冒险。
印度仿制药公司兰伯西前员工萨库尔在2005年就向美国FDA举报了这家药企的造假行为并提供证据,但直到2013年,才终于进行了法庭听证,最后只不过是达成和解(赔钱了事),没有任何人需要负刑事责任。
8年,在一个人一生中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得到的还是这种结果。
美国FDA某任国际药物质量部部长说,“我这个人喜欢祈祷。但是某个批次的药是好药,不该成为我们祈祷的内容。”
如果监管不到位,普通人又能寄希望于什么呢,祈祷?
跟ChatGPT交流了一番,它说:
现代社会并不是靠“所有产品都可靠”运行的,而是靠“出问题的概率被控制在大多数人尚可承受的范围内”运行的。
我仔细品味这句话。好吧,欢迎来到现实世界大冒险。









11 50
听播客第十个年头了。
在声音的陪伴中听着喜欢的主播离婚,从北京搬到上海,结婚,生娃……
在声音的陪伴中听着喜欢的情侣搭档从沪漂到北漂到回老家,从结婚到离婚……
每个人生活的B面,又如何为外人道呢?
今天跟同事聊天,说起工作上的糟心事,提到职级比我们高的同事姐姐,虽然把这一摊烂事安排给我们,但也有别的难干的活。
我说:“也不是羡慕她,毕竟她也有她的难处。”
时不时进行感恩日常练习,心态很平和。
在声音的陪伴中听着喜欢的主播离婚,从北京搬到上海,结婚,生娃……
在声音的陪伴中听着喜欢的情侣搭档从沪漂到北漂到回老家,从结婚到离婚……
每个人生活的B面,又如何为外人道呢?
今天跟同事聊天,说起工作上的糟心事,提到职级比我们高的同事姐姐,虽然把这一摊烂事安排给我们,但也有别的难干的活。
我说:“也不是羡慕她,毕竟她也有她的难处。”
时不时进行感恩日常练习,心态很平和。

11 00
还是要多做自我觉察。我真的太容易被突如其来的临时工作trigger到。
本来年底加班事情多,晚上7点过突然被同事拉到一个群里,说需要写xxx调研报告,分成不同方向给大家分了工,明天10点就要。
leader也在这个群里,表示时间紧张,辛苦大家。
打开文档一看,我已“崩溃”,这东西怎么可能是几个小时能写出来的(真好笑)。
但其实我心底里的焦虑已经开始释放,大概皮质醇在迅速上升,心想着:手头还有这么多事,这个任务这么紧张,还不知道要怎么弄……
但幸好,我马上给同样在这个临时群的另一名同事打了个电话,询问这个工作内容。
他“分析”了一下,认为大概率是派活儿的这位需要这样一份报告推进他自己的工作——又正好是leader看重的,然后表示,就明天上班了去写呗。
结束通话后我的焦虑值极速下降。
对啊!这活儿本来就跟我没关系,但毕竟是leader同意让我们一帮人来帮这个忙,实在是难以推脱。但,时间紧迫,而我手头的事对我来说更重要,那这个活儿就差不多得了呗。
毕竟,就算我写得再尽职尽责,leader大概是不会记得的,完全就是给派活儿的这位免费“打工”。
我还是太“本能”地…总是接收到一项工作任务后就开始“烦恼”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好。
真是不被看见的牛马潜质啊。
再这么下去,脏活累活都拥过来了,能怪谁。
长个记性!
本来年底加班事情多,晚上7点过突然被同事拉到一个群里,说需要写xxx调研报告,分成不同方向给大家分了工,明天10点就要。
leader也在这个群里,表示时间紧张,辛苦大家。
打开文档一看,我已“崩溃”,这东西怎么可能是几个小时能写出来的(真好笑)。
但其实我心底里的焦虑已经开始释放,大概皮质醇在迅速上升,心想着:手头还有这么多事,这个任务这么紧张,还不知道要怎么弄……
但幸好,我马上给同样在这个临时群的另一名同事打了个电话,询问这个工作内容。
他“分析”了一下,认为大概率是派活儿的这位需要这样一份报告推进他自己的工作——又正好是leader看重的,然后表示,就明天上班了去写呗。
结束通话后我的焦虑值极速下降。
对啊!这活儿本来就跟我没关系,但毕竟是leader同意让我们一帮人来帮这个忙,实在是难以推脱。但,时间紧迫,而我手头的事对我来说更重要,那这个活儿就差不多得了呗。
毕竟,就算我写得再尽职尽责,leader大概是不会记得的,完全就是给派活儿的这位免费“打工”。
我还是太“本能”地…总是接收到一项工作任务后就开始“烦恼”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好。
真是不被看见的牛马潜质啊。
再这么下去,脏活累活都拥过来了,能怪谁。
长个记性!
7 00
三四年过去了,看朋友圈里在学术圈深耕的人分享的科研成果,大多还是毫无新意的重复(但人家说不定乐在其中),无非是换了个xx, xx, 或xx。
上周跟去年入职的同事聊天,说我刚来的时候跟上级讲,我觉得学术圈做的东西太虚了(大多是自娱自乐),想要做出点真正的让人有价值感的东西。
现在想起来这段话真的很想扇自己。
或许我最大的痛苦来源是不认同。
不认同他们所谓的套路,不认同弄虚作假,不认同文字游戏……
是这个世界太荒谬,还是我太格格不入了?
同事说,我们这样的人应该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
上周跟去年入职的同事聊天,说我刚来的时候跟上级讲,我觉得学术圈做的东西太虚了(大多是自娱自乐),想要做出点真正的让人有价值感的东西。
现在想起来这段话真的很想扇自己。
或许我最大的痛苦来源是不认同。
不认同他们所谓的套路,不认同弄虚作假,不认同文字游戏……
是这个世界太荒谬,还是我太格格不入了?
同事说,我们这样的人应该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
13 30
古人如何知道地球是球体(凸体的平面投影是圆形),
再基于简单的数学(几何)知识计算地球大小(夏至日的两地距离与太阳高度角),
计算地月距离(月全食经历的时间与月球公转时间之比),
计算月球大小(月球升起时间与地球自传时间之比),
计算地日距离(月相中半月出现的时间与新月-满月中间点的偏差),
计算太阳大小(日全食中月球与太阳的大小差不多),
得知行星轨道形状是椭圆(开普勒确实很天才),
……
看完的疗效包括:
深感人类的智慧与渺小(因为宇宙的广阔),
知识的积累和传承确实重要,
沉浸式感受科学之美,暂时忘却尘世间的纷纷扰扰,忘却打不完的工,
……
年少时学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定理时,怎么不多讲讲人类的来时路呢?多有趣啊。
再基于简单的数学(几何)知识计算地球大小(夏至日的两地距离与太阳高度角),
计算地月距离(月全食经历的时间与月球公转时间之比),
计算月球大小(月球升起时间与地球自传时间之比),
计算地日距离(月相中半月出现的时间与新月-满月中间点的偏差),
计算太阳大小(日全食中月球与太阳的大小差不多),
得知行星轨道形状是椭圆(开普勒确实很天才),
……
看完的疗效包括:
深感人类的智慧与渺小(因为宇宙的广阔),
知识的积累和传承确实重要,
沉浸式感受科学之美,暂时忘却尘世间的纷纷扰扰,忘却打不完的工,
……
年少时学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定理时,怎么不多讲讲人类的来时路呢?多有趣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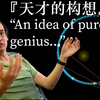
【官方双语】陶哲轩访谈(一):宇宙尺度阶梯_哔哩哔哩_bilibili
6 20
想了解某位哲学家的思想吗,请同时了解其副作用,后果自负。
1:38:35 摘录:
------
There's a common metaphor given about philosophy.
Philosophy is often compared with medicine that it has the power to cure our souls and societies.
And I think that's a quite apt metaphor, but just not taken far enough.
Because just as medicine has side effects, so do philosophy.
And I wish that philosophers wrote on the side of their books the unwanted side effects of their philosophies a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did on their drugs.
Warning, disdain for the material world if you take too much of these platonic dialogues in one sittings.
Caution, more than one dose of Niezsche a day makes patients with pre-existing conditions descend into uncontrollable rage.
Side effect, erectile dysfunction if you take these Buddhist sutras too seriously.
Attention, inability to form coherent sentences if you read too much adorno in one sitting.
Just as drug will course through your veins and infiltrate your entire system, Drard's ideas will latch themselves onto your psyche and colonize your worldview, so we must ask, what are the side effects of engaging Drard?
I've presented to you the red pill, but as any honest merchant, I must also tell you why you should take the blue pill instead.
关于哲学有个常见隐喻。
哲学常被比作能治愈灵魂与社会疾病的良药。
此喻虽贴切,且未言尽其质。
正如药物皆有副作用,哲学亦然。
我期盼哲学家能在著作扉页标注其思想的“不良反应”,如同药企列明药物风险。
警告,过量阅读柏拉图对话录可能导致物质世界厌恶症。
注意,尼采著作日服超过一剂,易诱发潜在心理疾病患者躁狂发作。
副作用,过度参悟佛经或致生命动能萎缩。
警示,连续服用阿多诺理论可致语言系统崩解。
正如药物会随血液渗透全身系统,基拉尔的思想亦将锚定你的精神世界,殖民你的认知图式,因此我们必须追问,接受基拉尔思想治疗将产生何种副作用?
我已呈递红色药丸,但作为诚实的药剂师,我必须告知你为何该选择蓝色药丸。
1:38:35 摘录:
------
There's a common metaphor given about philosophy.
Philosophy is often compared with medicine that it has the power to cure our souls and societies.
And I think that's a quite apt metaphor, but just not taken far enough.
Because just as medicine has side effects, so do philosophy.
And I wish that philosophers wrote on the side of their books the unwanted side effects of their philosophies a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did on their drugs.
Warning, disdain for the material world if you take too much of these platonic dialogues in one sittings.
Caution, more than one dose of Niezsche a day makes patients with pre-existing conditions descend into uncontrollable rage.
Side effect, erectile dysfunction if you take these Buddhist sutras too seriously.
Attention, inability to form coherent sentences if you read too much adorno in one sitting.
Just as drug will course through your veins and infiltrate your entire system, Drard's ideas will latch themselves onto your psyche and colonize your worldview, so we must ask, what are the side effects of engaging Drard?
I've presented to you the red pill, but as any honest merchant, I must also tell you why you should take the blue pill instead.
关于哲学有个常见隐喻。
哲学常被比作能治愈灵魂与社会疾病的良药。
此喻虽贴切,且未言尽其质。
正如药物皆有副作用,哲学亦然。
我期盼哲学家能在著作扉页标注其思想的“不良反应”,如同药企列明药物风险。
警告,过量阅读柏拉图对话录可能导致物质世界厌恶症。
注意,尼采著作日服超过一剂,易诱发潜在心理疾病患者躁狂发作。
副作用,过度参悟佛经或致生命动能萎缩。
警示,连续服用阿多诺理论可致语言系统崩解。
正如药物会随血液渗透全身系统,基拉尔的思想亦将锚定你的精神世界,殖民你的认知图式,因此我们必须追问,接受基拉尔思想治疗将产生何种副作用?
我已呈递红色药丸,但作为诚实的药剂师,我必须告知你为何该选择蓝色药丸。

100分钟解析模仿理论|勒内·基拉尔|一讲_哔哩哔哩_bilibili
5 12
我真的热爱学习吗?
小时候爱挺喜欢学数学的,但刚刚突然意识到,其实我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喜欢。
听旁人聊天说到身份证号码最后一位校验码,猜测应该是用计算公式得到一个数除以11得到余数的过程。
联想到小时候关于整除的一些规则,比如一个整数能否被3整除,将其各个数位上的数字加起来能否被3整除,即可判断。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没有想过这个规则的逻辑,但其实并不算难:
10 ≡ 1 (mod 3)
10的幂次除以3的余数都是1
任何除以3的余数是1的整数,相乘后得到的整数,除以3的余数还是1
费曼说:
"What I cannot create, I do not understand."
所以,学习与思考是一种天赋吗?
刚刚跟ChatGPT交流上述内容发现,我所以为的“喜欢数学”,并不真的是喜欢过程/本质,更多的是喜欢做题,喜欢结果罢了。
记住规则,能把题目做出来,很快乐;
越学越难,做不出题目,就不喜欢了。
一种虚假的喜欢。
一种痛苦的来源。
在即刻上分享播客或读书笔记的那种快乐,才是在被世俗标准拉扯之外自己愿意就能得到的快乐啊。
小时候爱挺喜欢学数学的,但刚刚突然意识到,其实我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喜欢。
听旁人聊天说到身份证号码最后一位校验码,猜测应该是用计算公式得到一个数除以11得到余数的过程。
联想到小时候关于整除的一些规则,比如一个整数能否被3整除,将其各个数位上的数字加起来能否被3整除,即可判断。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没有想过这个规则的逻辑,但其实并不算难:
10 ≡ 1 (mod 3)
10的幂次除以3的余数都是1
任何除以3的余数是1的整数,相乘后得到的整数,除以3的余数还是1
费曼说:
"What I cannot create, I do not understand."
所以,学习与思考是一种天赋吗?
刚刚跟ChatGPT交流上述内容发现,我所以为的“喜欢数学”,并不真的是喜欢过程/本质,更多的是喜欢做题,喜欢结果罢了。
记住规则,能把题目做出来,很快乐;
越学越难,做不出题目,就不喜欢了。
一种虚假的喜欢。
一种痛苦的来源。
在即刻上分享播客或读书笔记的那种快乐,才是在被世俗标准拉扯之外自己愿意就能得到的快乐啊。
7 20









